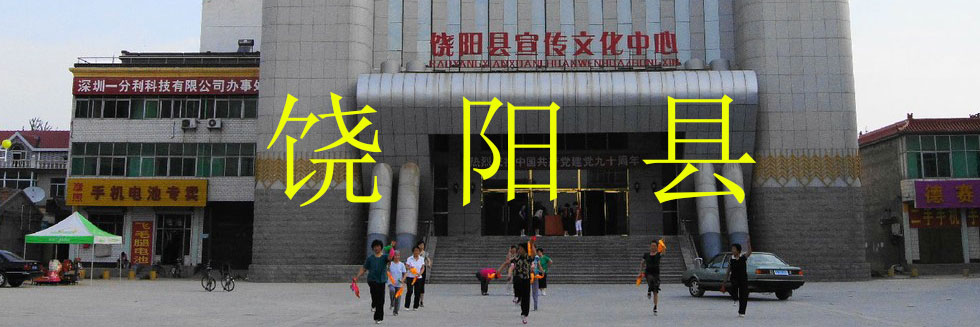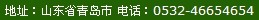|
新泰,是一片古老而美丽的土地。这里被山带河、风光秀美,历代在此建邑置县,经营相继。数千年来,帝王巡幸,圣贤流连,名臣牧守,可谓风云际会,兵戎胶葛,演出过不少威武雄壮的活剧。新泰本土也英彦辈出,名贤不绝,其人其行,犹如日月行天,令人仰止。漫漫历史长河,积淀成灿烂的新泰古代文化。下面,便让我们沿着这条悠悠长河,对新泰的历史作一番追溯与巡礼。 “新泰人”,是中华大家庭中资格较老的成员之一。年在新泰乌珠台村发现一枚旧石器时代晚期“智人”牙齿化石。据专家鉴定,这枚牙齿属于少年女性。这位娇美的乌珠台少女从历史深处冉冉走来(据《齐鲁晚报》.1.7所刊西原《并不丑陋的少女》一文称:乌珠台少女的“外貌特征当与现代人没有多么显著的差别,智力方面也是如此”),说明了早在5万年以前,新泰就有人类在此生息、繁衍。考古调查发现,柴汶河两岸有不少原始社会遗址,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皆有遗存,并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有代表性的器物。由此可知,早在四五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已在这里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揭开了东方人类文明的序幕。 根据当代史家的最新研究:上古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多与新泰一地有着密切的关系。如黄帝轩辕氏部族以龟为图腾,其族主要活动在泰山与汶泗流域,新泰之龟山便是轩辕族的一个地理标志。世传之尧都平阳,亦当在新泰,而非旧说之山西临汾。“平阳”盖因处平河(可能即柴汶河或其支流)之阳而得名。春秋时鲁置平阳邑,即沿用尧都旧名(以上问题,详见温玉春《黄帝氏族起于山东考》,载《山东大学学报》年第1期;及温玉春、曲惠敏《少昊、高阳、高辛、陶唐、有虞诸氏族原居于今山东考》,载《管子学刊》年第4期)。 相传,夏代曾将全国划为九州,新泰属于徐州之域。根据《禹贡》的记载:“海岱及淮惟徐州。”说明当时从海至泰山以及淮河都属于徐州。由于未见实物资料,夏代新泰的历史已难知其详,但根据历史学者的推考,在公元前五千年至公元前二千年的漫长历史时期内,泰山地区一直是当时全国文化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域,创造了自成体系的文明(万昌华《先商泰山文明述略》,载《泰安师专学报》年第4期)。新泰亦当属于这个先进文化区的一个组成部分。 商周时期,今新泰地曾分别有杞国、菟裘、淳于等小国先后存在。杞国为姒姓,夏禹后裔所建,殷商时已建国,周代封禹后东楼公于杞(今河南杞县),西周厉王时(前年前后),杞谋娶公率国北迁,立足于齐鲁两国之交的新泰一带,后来由于鲁国的侵伐,杞又再度东迁诸城一带(详见郭克煜《杞国迁居山东问题》,载《齐鲁学刊》年第4期)。杞作为一个东方小国,在大国争霸、弱肉强食的局面下艰难生存,未免凄凄惶惶,因此“杞人忧天”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有名故实。清代咸丰年间,新泰境内曾出土了多件青铜器,铭首皆有“杞白(伯)”字样,经当时著名学者许瀚考证,定为周代杞国东迁新泰时所制之物。这堪称是杞国建都新泰的历史见证(关于杞国地域问题,近年王恩田先生提出新见,认为先秦之杞国有二,一为商封之杞,立国于今新泰一带,战国时亡于楚;另一为周封之杞,初封于河南,东迁缘陵,后亡于齐。两国各具本末,不容混淆。其论与传统认定周杞东迁新泰不同,详见所著《从考古材料看楚灭杞国》)。周代初期,封周公世子伯禽于曲阜,曰鲁。当时东夷各国仍盘踞在山东东部和东南部的山区内,继续进行着抗周斗争。今新泰部分地区也在东夷势力范围内。为此伯禽在费地誓师,向徐戎、淮夷发动大进攻,将其部落逐往淮水之南。于是鲁国的疆土,向东方大为扩张,泰山已成为鲁国的望山,新泰境的龟山、徂徕、新甫与蒙阴境的蒙山,也都收归鲁国的版图。鲁君便令伐徂徕、新甫二山的松柏,建造雄伟的路寝、正寝、新庙,鲁国的宫殿才逐渐完成(参何光岳《周源流史·鲁国的来源和迁徙》)。到了春秋时期,鲁国开始在新泰设置城邑,《春秋》记载:“宣公八年(前),城平阳。”晋杜预注曰:“今泰山有平阳县。”鲁国所建的平阳邑,故址在今市区附近,俗称西故城,故新泰又称平阳。虽以后历代的地方行政建置屡有变更,但这里作为新泰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位置却一直没有变动过。另外,新泰西北境的梁父邑与菟裘邑,也是春秋时代的著名城邑。 在万马逐鹿、群雄竞起的春秋战国,新泰成为齐、鲁两国频繁争夺的地区。除了兵戈相交,一些折冲樽俎的外交活动也发生于新泰。鲁定公十年(前),鲁定公于齐景公会于夹谷,孔子以相礼的身份随同鲁君出席盟会,迫使齐人归鲁龟阴等田。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夹谷会盟”。夹谷故址即在今新泰境内,据明嘉靖《泰山志》卷二载:“岳东南地曰谷里,古夹谷也。” 先秦时期,是新泰英杰竞出、群星璀璨的时代。和圣柳下惠、乐圣师旷、奴隶起义领袖柳下跖、名儒林放、名相鲍叔牙,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柳下惠为鲁国大夫,食邑柳下(今新泰柳里),以崇尚礼节闻名于世,深为孔、孟所推崇,称为“圣之和者”(《孟子·万章下》),至今新泰还有“和圣墓”遗迹;柳下跖以九千人反抗诸侯,横行天下,被誉为“名声如日月,与舜禹俱传而不息”(《荀子》);鲍叔牙与管仲一同辅佐齐桓公开创霸业,“管鲍之交”被传为千古佳话,新泰鲍庄便为这一代名相的故里所在;师旷曾任晋国乐师,为春秋一代乐圣,其长眠之地,乃在新泰之北师店;林放为孔子弟子,以知礼著称,孔子曾将林放比于泰山,有“泰山不如林放乎”的赞誉之词,城以人重,他的名字已与放城紧密相连。另外,梁父颜涿聚也是春秋末期的名人,其人先为侠盗,后受教于孔子,仕齐为大夫,后在齐晋之战中殉职,史称之为“梁父之巨盗,卒为齐之忠臣”(参见《吕氏春秋·尊师》、《后汉书·左原传》),这些乡邦贤哲,其行令人高山仰止,因而赢得新泰人民的世代敬仰。 新泰的经济与文化,先秦时便已兀现史册。据史家研究,泰山一带为较早进入原始农业时代的地域,故而山川崇拜极为盛行。当时齐地“八神”之祀,第二神曰“地主”,便祭祀于新泰境内的梁父山上。这一祀典一直延续到秦汉(汉成帝时始被罢省)。“封禅”之说,也在先秦开始出现,据《管子·封禅篇》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其中所述十二古帝王,禅于新泰境内之云云山者凡九家。《管子》的记载虽可能仅是远古的传说,但反映了新泰山川在当时信仰中已具有较大影响。周代甫国(即吕国,封在河南新蔡)人东迁新泰,加速了对新泰山林的开发,新甫山便因甫人迁居而得名(据何光岳《炎黄源流考·吕国的形成和迁徙》)。徂徕、新甫都以林木茂盛著称,在《诗经》中便有“徂徕之松,新甫之柏”的赞美诗句。又境内敖山(又名具山,一说具、敖为两山),春秋时曾列入鲁之祀典,晋国大夫范献子出使鲁国,曾向鲁人问及二山之名(见《国语·晋语九》)。可知具敖在当时已驰名邻邦,播于众口。此时的一些名人踪迹、艺文遗事,也大多与新泰名山有着不解之缘。一代圣哲孔子“伤政道之凌迟”,望龟山而作歌,其复登彼邱陵,攀援梁父,赋《邱陵歌》而寄感;曾子耕泰山下,逢天雨雪不得归,思其父母,而有《梁父吟》之作,历代传唱,遂为乐府名篇。如果说先秦时代的新泰文化,乃是以名山文化为主体,或非不经之论。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地方施行郡县制。新泰境为当时薛郡辖地。《秦集史·郡县志》云:“《汉书·地理志》:鲁国,故秦薛郡。谭其骧曰:……(郡)北界凡《汉志》泰山属县计入鲁、东平二国之间者,悉当在界内。”可证新泰时为薛郡鲁县地。 秦始皇为了炫耀其威德,乃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前)“登于泰山,周览东极”。封祀岱顶后,又在今新泰境内的梁父山上举行禅礼。始皇并于梁父建畤以祀“地主”神。所谓“畤”,系古时祭祀天地五帝的固定坛址,近代学者瞿宣颖《中国社会史料钞》中指出:“秦之建筑足以代表其特殊文化思想者其惟畤乎。”明人刘孝有《秦畤》一诗:“梁父东巡地,青鸾翊翠华,……深幽询往迹,石表半泥沙。”便是对这一新泰封禅史迹的咏叹。 楚汉之争,新泰亦为鏖兵之所。汉将灌婴攻下邳,击破楚骑于平阳,即此。汉朝建立后,继续推行秦之郡县制度,在今新泰境置东平阳县,属兖州泰山郡,故城在今市城南部,俗称南故城。与此同时还在今县西境设置两县,一为梁父,一为柴城。梁父县置于汉武帝时,故址在今天宝镇古城村,今城垣尚存。柴城故城在今柴城村。王莽代汉,樊崇所率亦眉军曾据今新泰境内之徂徕山抗拒官府。至东汉初期,平阳因遭战祸波及,户口减少,建武六年(30)汉光武帝诏令“县国不足置长吏者并之”(《后汉书·世祖纪》),乃并平阳于梁父县(按《新泰县志》称“省入南城”,不确,今以《后汉书》诸羊传推之,当是省入梁父);东汉中末叶,因县内羊氏、鲍氏诸家族崛起,于是恢复平阳建置(《后汉书》称羊续“泰山平阳人”,知是时已复置平阳)。 西汉武帝统治时期,汉朝国力达到极盛,武帝为了显示他的文治武功,一生八次封禅泰山,报功于天,在新泰频频留下其翠华鸾踪。据《新泰县志·古迹》记载:汉武帝东封至新甫,“见仙人迹,建离宫于上,遂改为宫山,筑望仙台。”新甫山附近甘露堂、望仙台、迎仙殿、侯城、武帝碑,都相传是这位一代雄主的驻跸遗迹。武帝死后,宣帝本始二年(前72)“令武帝巡狩所幸之郡国”皆立孝武庙,泰山郡之孝武庙即立于新甫山。西汉末季,在郡国之宗庙相继罢废,新甫武帝庙却世代修复,直延续至明清,实为仅见。“犹疑云璈奏,想象天马歌”。汉武帝在新甫的遗事轶闻,更成此后千余年中词客感慨咏怀的题材。 秦汉时期,新泰的经济也趋于繁荣。自战国以来,齐鲁即以盛产桑麻著称,至汉愈盛,有“齐鲁千株桑麻”之称,其种植量居全国第一。新泰即为其主要产地之一。清人卢綋在《丝枲吟》诗序中曾追述这一史实:“《禹贡》青州之贡,记岱畎丝枲,考志,新泰皆岱畎地,而丝枲之产,新尤夙最饶。”汉武帝时,于泰山下筑渠以引汶水,灌溉田地万顷,小汶河流域的新泰农业得到较大开发。 汉代新泰文化也引人瞩目。儒学在汉初获得恢复和发展,至武帝时并登上了统治地位,成为儒学的黄金时代。司马迁所记汉初五经七家八位经传大师中,其中一位便是新泰人高堂生。高堂生为齐公族高傒之后,傒封于高堂(今新泰龙廷),因以为氏。生汉兴为博士,以礼书十七篇授瑕丘萧奋,后世言礼者咸宗之。高堂生卒后,即葬于故里,至今新泰城东玉皇山下,还有这一代儒宗的丘垄。汉代新泰的艺术也有很高的成就,师旷墓的汉阙雕刻,造型生动,雕制精美,便是这一时期艺术水平的真实反映。在清代金石学家叶昌炽《语石》和现代著名作家鲁迅之《丙辰日记》(年12月书帐)中都曾提及这一艺术珍品。 两汉时期,是新泰英彦辈出、乡贤群起的时代。羊氏、鲍氏都在这一时期崛起,而在纷纭的汉代政坛上,留下其风驰当年的仕踪宦迹。 羊氏为春秋晋公族羊舌氏之后,秦乱徙居泰山,至汉“七世两千石卿校”。羊侵于汉安帝时为司隶校尉,其子儒,桓帝时为太常。儒子续,为灵帝时名臣,历官南阳太守,为政清廉,其悬鱼拒贿被传为佳话,梁父城旧有“羊续碑”遗迹(《魏书·地形志》)。宗人羊陟,历官河南尹,禁制豪强,刚直不阿,为一时清流领袖。鲍氏为司隶校尉鲍宣之后,自上党徙泰山平阳,宣八世孙信,汉末为济北相,首倡迎曹操入主兖州,为曹魏奠基立下了汗马之功。 在东汉后期,还有两位历史名人曾在新泰留下其遗踪芳躅。学者蔡邕光和间以事流亡,往来依泰山羊氏,积十二年。邕卒后,羊氏复将其收葬于蒙山。名臣诸葛亮之父诸葛珪曾官梁父尉、泰山郡丞,亮曾从父任上,读书梁父山下(《忠武侯祠墓志》),后亮“好为《梁父吟》”(《三国志·诸葛亮传》),即缘于少年时期的这一生活经历(据清人程穆衡《燕程日记》所载:新泰葛沟桥,相传其地即武侯故居)。 三国鼎立,新泰在魏境。魏沿置东平阳县,仍属兖州泰山郡。 曹魏时期,平阳人高堂隆显声于朝野。隆为高堂生之后,承今文经之家学,精通古代之礼制,仕魏累官散骑长侍,以廉洁清正、直言敢谏著称,他曾在上魏明帝疏奏中言称:“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独陛下之天下也。”显现了其民本思想的精华。高堂隆还在天文、数学方面有突出贡献,英国科学家李约瑟(J.Needham)曾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两次提到他的成就。 晋朝代魏后,羊祜取新甫山、泰山之首字,表改平阳为新泰县,属泰山郡(晋惠帝时割属东安郡)。自此开始出现新泰之名,并一直沿用至今。 随着西晋王朝的建立,新泰羊氏家族也如日丽中天,达到极盛。羊续孙女徽瑜,为司马师之妻。在司马氏代魏的政治变更中,羊祜、羊琇等人立下了重要功勋。故晋立,羊氏“宠遇甚厚”。徽瑜之弟羊祜,泰始中为尚书左仆射、卫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后授征南大将军,坐镇襄阳十年,江汉归心,为攻取东吴,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祜从弟琇,封甘露亭侯,累迁中护军,加散骑常侍。至今留存的新泰《孙夫人碑》,便是晋初羊氏家族的遗物。 晋武帝死后,西晋宫廷斗争激烈复杂,羊氏卷入其中,其命运沉浮不定。羊玄之之女羊献容被立为晋惠帝皇后,在八王之乱中被五废五立,最后在汉灭西晋之役中,为刘曜所掳,立为皇后。及晋室南渡,中原冠盖相随,羊氏一些族人纷纷渡江,仕于东晋。羊曼、羊鉴、羊聃、羊楷、羊权、羊绥、羊贲、羊不疑、羊玄保、羊徽、羊欣都在东晋及南朝政坛上各有影响。 西晋覆灭后,北方进入十六国时期。今新泰境先后为后赵、前燕、前秦、后燕、南燕所领有。南燕将兖州刺史治所设于梁父,新泰一度成为兖州的政治中心。在兵戈频仍中,新泰种植业仍有所发展。晋末学者伍缉之从刘裕伐燕,所著《从征记》中曾记叙到新泰青沙岘“木皆栌杏”的景象。 在南北朝分裂对峙时期,今新泰地先为南朝宋,后为北朝魏、东魏、北齐、北周所领有。南朝宋时,境内新泰县隶徐州东安郡,梁父县隶兖州泰山郡。北魏时新泰隶北徐州东泰山郡。梁父县自古城村移置镇里(《泰山道里记》“徂徕山南”一节)。梁父一度改名岱山。又北魏于南青州东安郡亦置有同名之新泰县(即今蒙阴县地),北齐天保中与北徐州东泰山郡之新泰县合并(《新泰县志》云省“蒙阴”于新泰,不确,兹据《续山东考古录》“新泰”、“蒙阴”两节属辞)。此后七百年中,今蒙阴县境一直为新泰县之辖地。 南北朝时,新泰羊氏仍活跃政坛,特别是羊规之一系,更在故里有较大影响。羊规之为宋祭酒从事,后出为任城令;元嘉魏师伐宋,规之归降,魏拜其为雁门太守,赐爵钜平子,自是羊氏族中一支仕于北朝。规之子祉,历官梁、秦二州刺史,曾重开褒斜,复通石门,对西北地区经济文化的开发作出了重要贡献。至今陕西汉中还存有北魏《石门铭》刻石,铭记了羊祉这一懋功勋业。祉子侃有伟略,仕魏为泰山太守,以愤尔朱荣大杀朝士,乃起兵叛魏附梁,后在梁侯景之乱中抗击叛军,功勋懋著。侃兄羊深,历官魏中书令、御史中尉、东道军司,在高欢篡魏的政治更替中,力拒高氏,最后在泰山博县商王村之战中,为高欢军所破,阵中遇害。深子肃,以学知名。齐武平中入文林馆撰书,出为武德郡守。羊烈历仕东魏、北齐、历官义州刺史。 在羊氏故里,羊族文物多有遗留。北魏熙平间所立《兖州刺史羊使君(灵引)碑》,宋代已屡为金石学家所著录(见《集古录目》及《宝刻丛编》卷二十)。近三十年来,地不爱宝,在新泰境内先后出土了羊祉夫妇、羊深夫人、羊烈夫妇共五方羊族人物墓志,为探究历史上这一士族的变迁兴衰提供了重要的史证。 在文化领域,这一时期的新泰也值得一叙。羊祜不仅为政治名臣,而且在文学上也卓有成就,有“文为辞宗”之誉。学术思想方面,羊祜著有《老子传》,羊烈曾注佛道经七十余卷。又羊氏为书法世家,羊欣承二王余韵,善行草,尤工隶书,被称为“子敬(王献之)之后,可以独步”。且在书法理论与书法史论上颇有造诣。羊氏族人中羊固、羊忱也以善书著称。今新泰所出羊氏墓志,字迹多质朴刚健,当是羊氏书风的体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道教在新泰广泛传播。羊氏族人大都笃信佛教,影响所及,遍及民间。佛寺建筑,佛教造像及摩崖刻经在新泰多处出现。西都玉泉寺,创始于晋;徂徕光化寺,兴建于北魏,后者更成为泰山之南的丛林名刹。至今徂徕山上还有北齐武平时梁父县令王子椿所刻佛经,为著名的文物遗存。又据《魏书·地形志》记载,北魏时期梁父县建有贞女山祠,为境内名胜。 隋统一后,新泰初属莒州,大业初复属沂州。梁父县治移于今泰安之东梁父,属兖州。隋末社会极为动荡,而新泰一邑相对安定。据《崇庆寺碑》记载,唐新泰令张文珪之父,隋大业末年弃官逃亡新泰谷里,为新泰士人羊彪所礼重,得全身家。可知当时新泰幸免兵燹,而成为民众避难之所。唐代实行道、州、县三级行政体制,县隶河南道沂州琅邪郡。武德间曾属莒州,贞观间复归沂州。同时并撤梁父县,并入兖州之博城。 唐代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空前繁荣。这些都在新泰历史资料上有所体现。贞观间,兖州高僧释慧斌住锡梁父存道寺,博听经论,誉彰禅林,太宗下敕征之京师。元贞间高僧释怀晖卓锡徂徕山,四方禅子多来此请问。新泰一些名刹也多于此时构建,县城崇庆寺,为垂拱三年()新泰令张文珪修建,规制宏敞,登仕郎芮智璨为撰记碑,此刻为新泰古代名碑之一,曾著录于《唐文拾遗》、《八琼室金石补正》等文史名著。又寺内开元十五年()经幢,为八棱形,每面皆镌佛像及幢主名氏,《语石》卷四中曾称:所见八面造像之幢,以新泰之幢“为甲”。可见新泰工匠的艺术匠心。创建于开元七年()的谷里明光寺,亦为当时岱下胜区,至今唐代残碑犹存。另外值得叙及的是,在开元年间,著名诗人李白曾携家卜居沙丘(今新泰古城),与孔巢父等人隐居徂徕山,酣歌纵酒,时号竹溪六逸。李白在此留下了许多著名诗篇,堪为新泰的山水增辉。 席卷中原的唐末黄巢大起义,曾一度转战泰山,新泰南部山区的黄山寨,便世代相传为黄巢义军驻扎之处,近年曾于寨址多次出土矛、剑等兵器。虽沉沙折戟,犹见战争酷烈。 五代新泰仍属沂州。宋时行政体制以路代道,新泰属京东路沂州。据《元丰九域志》卷一载:“新泰,(沂)州西一百七十里。二乡。有敖山、汶水、沂水。” 北宋新泰制瓷业十分兴盛,汶南、碗窑头等地皆有这一时期的瓷窑遗址,其制瓷工艺十分娴熟。这大大繁荣了地方经济。此时新泰还盛产硝石、石脑、炬火等矿石,“居人常采以为货”(《太平寰宇记》卷二十三)。各种民间文化活动也日趋繁兴,新甫山上的汉武帝庙,便是此时重建。宣和年间,宋廷以敖山有布雨之“灵异”,加封其山神,“敕赐庙额为孚泽,加封爵曰溥灵侯”(《新泰县志·古迹》)。时人又于孚泽庙东建齐鲁二侯庙(嘉靖《山东通志》卷十八),附祀春秋鲁献公、武公等。于是敖山声名大盛。又法云山正觉寺,也始建于北宋末期。留存至今的沂州新泰县三清庙平乐乡众题名碑拓本,反映了当时境内民间宗教活动之繁盛。 宋代理学盛行,教育发达,而被称为开理学之先河的著名学者孙复,其讲学泰山期间,曾卜居新泰城南。“孙村”即由孙复而得名。这大大促进了当地文化的发展。宋徽宗御制《大观圣作之碑》宣谕士子,并颁行天下州县,其一便刻石于新泰,其碑清代犹存(《语石异同评》卷八)。宋绍圣、元丰及宣和间,新泰人于天隐、梁赐、刘良佐、孙巾造、龚遂、常曾、苑当、刘苗、龚适等九人皆以进士入仕,显声科场。元丰进士常曾还撰有《新甫山记》(今存残文,见于《大明一统志》卷二十二),此篇是目前所知最早关于新甫山的专文。宣和进士龚适,县西南龚家村(今西周北公村)人,历官翰林承旨,今传其《游峙山》一诗,亦是关于峙山的最早文献。龚家庄西岭旧有龚学士墓,即龚适葬所。 宋徽宗时期,在山东爆发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宣和二年(),宋江与沂州知州蒋圆激战后,曾率余众“北走龟蒙间”(《蒋圆墓志铭》)。至今放城一带还有“马死峪”、“杀败岭”、“马头庄”、“马尾庄”等地名,相传为宋江与官兵鏖战的遗迹。 北宋末年,金军大举南侵,灭亡北宋,在“靖康之难”中慷慨殉节的兵部尚书孙傅,祖籍新泰楼德。楼德镇有孙傅之祖孙觐之墓,旧日楼德西寨门高揭石匾曰“孙傅故里”,便是为纪念这一名臣而设(参见路韧《楼德探古》,载《新泰日报》.4.23)。此后,金兵又不断南侵,攻掠偏安江南的南宋。建炎二年(),金将粘罕攻入京东,兵锋直抵泰山一带。山东民众在须城(东平)吴给、奉符(泰安)孙亿的率领下,聚义于新泰西北的徂徕山,并数度下山与金兵激战。南宋遥授“承议郎吴给充徽猷阁侍制,知东平府;朝奉郎孙亿直龙图阁,知袭庆府”(《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八)。但由于宋廷一意向金求和,无心北顾,加之金国不断加强对山东的军事扫荡,徂徕义军的处境日趋艰难。建炎三年()七月,金将乌延胡里改攻破泰山诸处山寨,徂徕义军失败,新泰遂全陷于金兵之手。但新泰境内的抗金斗争仍接连不断,原山西抗金义军首领李通、李成南渡投宋后,官至镇抚,他们念念不忘收复失地,派子弟潜回新泰秘密组织义军,坚持斗争。祖孙三代抗金受到宋室褒奖,后人称“元帅李家”。 金代新泰初属刘齐,齐帝刘豫以程巽为县令。后金废刘豫,新泰入金,隶山东西路泰安州。 在金世宗统治时期,国内趋于稳定。天德间王陟明任新泰令(按王陟明又作王广道,号醇德先生,通经学,其弟子周驰与党怀英有交,事见《中州集》卷七周驰传),清廉有为,著名诗人党怀英在《环翠堂》一诗中对其治迹予以高度称颂。金代新泰进士共有八人,其中刘述、刘造、刘进兄弟三人,皆于正隆间中试礼闱,传为科场佳话。又乡人张佑、储进皆以武功显,张佑从金军攻取大沫堌有劳,累迁定远大将军;储进金季应募即戎,以功授宣武将军、滋阳县尉。放城伽蓝静林寺,也初创于金代明昌间。 到了金代后期,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逐渐激化,一场席卷北方的红袄军起义在山东爆发。红袄军首领郝定,自称大汉皇帝,率部攻占新泰、莱芜、泰安等州县,称雄一时。此时山东、河北的地主豪强,在蒙古军不断侵扰、金军败退的形势下,也纷纷组织地主武装据地自保。石珪、时珍等人便先后于新泰起兵,在宋、金、蒙古的三角战争中鹰扬战场。石珪,新泰人,贞祐兵起,他率家乡子弟据险自保,曾归附刘二祖红袄军旗下。复大破李霸王兵于龟蒙山。嗣后珪率部投宋,为忠义军将。复降蒙古,为济、兖、单三州兵马都总管。最后在元光二年()曹州之战为金兵所破,珪被俘杀。刘原,新泰人,元初兵乱,其据地保障,一方赖之。时珍,天宝人,贞祐兵起,他据守天宝寨,地方帖然。仕蒙官至镇国上将军、右副元帅。 降于蒙古的大将严实入据东平后,新泰各支武装多归于严氏麾下,新泰遂为严氏所领有。在严氏父子相继称藩东平期间,一意求治,造成一个相对安定之社会环境,饱经战乱疮痍的新泰经济文化有所恢复,著名学者元好问在《严公神道碑》中记述:“不三四年,由武城而南,新泰而西,行于野则知为乐岁,出于途则知其为善俗,观于政则知其为太平官府。”先是在贞祐之乱中,徂徕山名胜古迹多遭兵燹,至是时珍父子对此加意恢复。北魏古刹光化寺在战火中“殿宇堂庑尽为灰烬”,珍为之重整寺宇,复其旧观,并由掌书记高诩写了碑记。时珍还在竹溪附近修建了二圣堂,今遗址犹存。其族人时正、时宥亦对徂徕胜迹多有兴复,今山中尚存时氏摩崖题记多处。 元朝建立,废除世侯,地方皆改为中央直辖,并将行政区改为路、府、州、县四级。先是元初于今蒙阴县境设“行新泰县”,蒙阴自北齐与新泰合并,自此始析离。中统三年(),割据山东之大将李璮起兵反元,旋败死于济南。据《马可波罗游记》(第六十一章)中记载,这场战争“双方伤亡惨重”。新泰便在是役中“为李璮所蹂躏”(《新泰县乡土志·兵事》),人民逃散。至元二年()元廷乃省新泰县于莱芜、行新泰县于沂水。今新泰地置改巡检司。后新泰人王显忠、吏员郭亨、王昕以县入莱芜,艰于输纳,力请具奏复置新泰,得获准,至元三十一年()遂复县置,仍属泰安州。新泰旧县衙前有古槐一株,新泰省入莱芜,古槐枯萎,新泰复置,枯槐抽枝发芽,人称“灵槐”。“灵槐复荣”遂为新泰八景之一。明代史学家谈迁在所著《枣林杂俎·中集》中,曾记述到这一有趣的地方掌故。 在蒙元一朝,兴起于唐宋的新泰制瓷业仍持续繁荣之局,其中碗窑头的窑址具有较大的规模。在遗址曾出土大量瓷器残片及窑具,其中以生活用具为多,制作已臻精美。 元代,新泰文化教育也渐次复兴。元初儒士鹿森在时珍的帮助下在徂徕山建二圣堂,以祀老、孔;至治年间,新泰道众复重建城东八里之名道观上清观(《大明一统志》卷二十二);延祐间,乡人在县北十五里南师店重建师旷庙,祀春秋乐圣师旷(《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一九九济南府新泰)。著名诗人王旭有《师旷庙》长诗颂之。都成为新泰著名胜迹。元廷重视教育,新泰县学便创立于元代至正年间(《大明一统志》卷二十二)。乡人郦克明、刘世科、孙甫皆登进士。又元廷曾诏“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有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元初名儒许衡曾隐居徂徕山中,读书讲学,匾其室曰“鲁斋”,学者称为“鲁斋先生”;元代中期,有进士贾氏讲学于云云山之云云亭,世称“贾氏书院”;元末,学者孙甫目睹政治黑暗,大变将起,遂隐居不仕,讲学于新甫之阳,一时士子翕然宗之。 元时,新泰人储企范与徐琛扬名于朝。储企范历任泰安、沂州知州,有文学,多惠政,修葺学校,士民怀服。徐琛为唐英公徐勣之后,历官亳州知府,先后见重于东平行台严实、太师月赤察,史称其有古侠士之风。他曾重修新甫山汉武帝庙,皇庆二年()其子徐彬为立碑记之。在今新泰羊流徐家庄,还有徐琛林墓,其墓地石仪造型稳重,刀法细腻,是石雕艺术之佳作。 元政权施行的残酷民族压迫与剥削,终于激起了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元末红巾军大起义于河淮迅速蔓延,至正十七年()二月,韩宋红巾军大将毛贵率师北伐,先后攻克泰安州及新泰等县。翌年元淮南行枢密院副使也速领兵反扑,攻破新泰,但不久即撤往河北。此后数年间,新泰一直由红巾军田丰部所控制。至正二十一年(),元将察罕帖木儿攻入山东,田丰投降,新泰复入于元,但此时元廷已呈现日暮途穷之势。数年后,吴王朱元璋部北伐,新泰等兖州以东诸县望风而下,新泰遂入于吴。元璋所署山东藩司征辟泰安士人刘复初署理新泰政事,后朱元璋称明帝,以台司汇荐,实授复初知县一职,成为朱明一朝的首任新泰县令。 明代,新泰隶属山东布政司济南府泰安州,并于县西上四庄(今关桥庄)设巡检司(《明史·地理志》)。又明时新泰编里二十有一(嘉靖《泰山志》卷四)。(明代新泰城区复原沙盘) 在明代,新泰城得到大规模修建,建成周围四里,连女墙高三丈五尺、广六尺的城池。旧城只有东、南二门,弘治间知县吴禧始辟西门,共三门,东曰通齐、南曰望鲁、西曰瞻岱(《古今图书集》职方典卷一九八济南府新泰),至此城池规模大备。后正德、万历、天启间屡加修葺。今新泰城区的规模,基本上就是在明城的格局上发展而成的。 明太祖收集流亡,减免赋税,使农业和手工业迅猛发展。新泰“地瘠民劳”,但在一些有为官员的努力经营下,也大大提高了生产力。洪武间知县邵恽勤廉有为,在任九年,“官无废事,野无流民”。成化年间知县高奉在任期间,教民种蔬菜以备荒,使新泰蔬菜业得到很大的发展,史称“新之有园圃者自公(高奉)始”。嘉靖知县刘宗礼亦亲治园圃,“自莳蔬菜”。万历年间,知县李上林于境内倡植桑麻,以救饥馑,在任五年,桑麻遍野,邑无逃亡。煤矿开采在明时也开始出现,至清代更发展为著名的煤田开采地之一。 在文化教育方面,明代的新泰也留下了较多可述的成绩。首先是《新泰县志》的创修,新泰一邑虽历史久远,但自古无志,嘉靖年间始由新泰学者孙述、李廷臣、崔克仁等人发凡起例,纂为志书,著名戏曲作家李开先为是书撰序,文中赞誉此志:“一方文献足征,百年信史有赖。”(《闲居集·新泰县志序》)万历、天启年间,知县王应修、赵希捰址直鹦尴刂尽H肭逯螅持沃匮罴谭肌⒖滴踔啬养气、宗之璠乾隆知县江乾达,光绪知县徐致愉皆曾有修志之举,为后世研究新泰历史,留下了无比珍贵的史料。孙述、王应修所修之志久已失传,但明人创修之功,实不可磨灭(附带提及:《新泰县志》[似为清初刊本]曾于江户时代之享保十年[]随商舶传入日本,并被著名的枫山文库所收藏。事详大庭修《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第三章中《方志持渡年表》)。王应修以诗文饰吏治,与县内士子诗酒唱和,留下了为数甚多的文学佳作。知县路升珍护古迹,尝树石以表羊流之墓。徐光前在《邑侯路公表晋太傅成侯羊公先茔墓碑》中称:“饶阳路公以名进士来令吾新,……慕古兴怀,伐宫山一片石,题于三羊墓畔,曰‘晋太傅成侯羊公先人之墓’。”皆关心文化,卓然可书者。明代沿袭旧制,于新泰设儒学,洪武三年()重建县学(《大明一统志》卷二十二)。万历年间,知县胡悦安复大修庙学,增广学舍,著名学者于慎行亲为此举撰碑,大加称颂。万历间知县吕志伊更亲主讲席,“视诸博士弟子犹弟子也,岁时课经术,论说义经,饘粥膏油不费不乏”(《新泰令吕宇衡墓志》)。另外,学者陈奇、吴希孟、徐登进先后司教新泰,皆兴教倡学,不遗余力,史称“新邑人文之盛自(正德间教谕陈)奇始”(《新泰县志·宦迹》。陈奇事迹,可参见明·张岳《赠年友陈士特司教新泰序》,载《明文海》卷二八○)。又嘉靖间新泰名儒王楫(松舟)设帐泰山投书涧,泰山阳明学巨擘李汝桂即出其门下。有明一代,新泰人才之盛,迈超宋元,其中崔文奎、徐光前等皆以科举入仕,显名于明;尹邦奇、刘实、安选、李廷厚、牛濩、徐之仪则游艺翰墨,驰声文场。 说到明代乡邦人物,则以四尚书声名最著。这四人分别是嘉靖朝工部尚书崔文奎,万历朝兵、刑两部尚书萧大亨,礼部尚书公鼐,天启朝兵部尚书秦士文。崔文奎力谏世宗崇道及兴献王祀典,深得时人仰慕;萧大亨莅官绝塞,在蒙汉和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公鼐为一代诗宗,其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声情的诗歌理论,对后世诗坛有重要影响;秦士文整顿军备,政绩卓著,惟因被卷入魏忠贤党争中,致令晚节不终,成为千古憾事。与萧、公、秦同时,还有一位解元进士徐光前,其历官交河、密云县令,兴利除弊,表现了高度施政才能。卒官之日,父老巷哭,樵夫牧儿,皆为陨涕。又四川按察佥事成功、广平府教授梁盈、嵩县知县王楫、福清知县赵秉、黔江知县张志道等新泰籍人士,亦皆有治迹惠政,流播人口。 明朝中末期,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明廷的盘剥日趋严酷,土地集中日加严重,自然灾害也为祸甚烈。如成化八年()“新泰大饥,人相食”(《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二○七济南府新泰)。特别是明神宗派遣税使、矿监,更是恣横骚扰,造成严重的社会危机。据北京出土之《新泰令吕宇衡墓志》记载:“矿税之役,邑(新泰)内骚然,穷民复有鬻妻子掉臂去者。”又神宗子福王之国,赐田达两万余顷,据安选《新泰侯王公生祠德政碑记》记载:“福藩王田派在新者百余顷,视邻封加倍。”当时蒙祸之烈,据此两条史料可窥一斑。除此之外,官府种种苛政亦厉于猛虎,时人曾谓:“新邑地瘠民贫,素乏盖藏,频苦大祲……且今一病于逃荒之包赔,一病于解役之苦累,一病于槽头之攀扰。”(天启《新泰县志后序》)虽有李上林、吕志伊、王应修等一二正直官吏奋起抗争,以纾民艰,但都难挽狂澜。李上林赴任“载家粟供飨餐食”,发赈有方,吏不能为奸,复力持“缓征薄赋”,以“郁伸毙起”。这样一位爱民如子的循吏,竟为官场所不容,“憾者乘间为蜚语中公”,上林被迫去职(事见李维祯《新泰令李公寿序》,载《大泌山房集》卷三十一)。万历天启之际,知县赵希捲鞘隼〗倌训男绿┍揖跋螅骸坝嗉何矗)承上命来牧兹邑,入其境,见城垣倾圮,村落萧条,……新民之疮痍未尽复,犹有凋疫状。”(天启《新泰县志后序》)故朱明一朝,新泰境内民变迭起,斗争不止。 正德年间,刘六、刘七率军数万攻破新泰,大破新泰知县刘瓒,焚毁城池而去。嘉靖年间,王堂率领的青州矿工起义军转战新泰,明都指挥杨纪追及于新泰龟山,王堂据山为固,大破官兵,击杀临清卫指挥佥事杨浩(《国榷》卷五二.《后鉴录》卷三)。 天启二年(),徐鸿儒在邹县发动白莲教起义,知县赵希挻颐π拗石城以拒义军,但区区石城,终无法抵御民变的烈火。崇祯年间,史东明、李青山等支农民军先后攻入新泰,同地主武装激战。崇祯十六年()“土寇”围城,乱矢射杀据城对抗的廪生董理。李青山起义聚众数万,威震东土,最后在崇祯十四年()十二月,于新泰石莱山,为明总兵刘泽清所破,李青山被俘遇害。在各支农民起义军冲击下,明王朝在新泰的统治已摇摇欲坠。 与此同时,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满族清政权,也对明朝发动总攻,不断杀入明境,大肆劫掠,腥风血雨,席卷中原。崇祯十五年(),清军大举入塞,进入山东,翌年兵锋掠及新泰,新泰生员张遇留率所部民军“知方军”,与八旗军展开肉搏,因众寡不敌,张遇留慷慨殉难,知方军一军尽没(事见《明通鉴》卷八九、《胜朝殉节诸臣录》卷十)。抗清英雄张遇留的事迹及所表现出的民族正气,得到了家乡父老的长期景仰。 在李自成起义的进军号角中,腐朽的明朝终被埋葬。李自成大顺政权定鼎北京后,任命大批官员分赴畿内、山东,接管地方政权;其中以周祚鼎为新泰县令。由于清兵入关,李自成仓皇撤出北京,山东局势一片混乱,当大顺地方政权纷纷败亡之时,周祚鼎仍率领一支孤军,同清兵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史载:“甲申()国朝(清)已定鼎燕京,‘李贼’所置‘伪’新泰令犹为贼守城甚力。”(《新泰县志·忠义》)面对来势汹汹的清军,周祚鼎毫不畏惧,严拒招降,誓死抗清,致使清山东巡抚方大猷在题本中哀叹:“新泰城小而固,……招抚再三,到底不服。”为了扑灭新泰城头的革命烈火,清军重兵压城,并勾结城内士绅发动叛乱,周祚鼎腹背受敌,大势已去,只得弃城而走。缙绅牛文等人“以城降”于清。新泰大顺军虽被满汉地主阶级所镇压,但他们坚守县城达四个月之久,是李自成在山东政权中为时最长的一个,在明末农战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 清初,新泰仍属泰安州。雍正二年()泰安升为直隶州,雍正十三年()再升泰安为府,新泰仍为泰安州、府的辖县之一,直至清末而未改。又雍正时新泰置三十三保,至乾隆时增为三十七保。 新泰在清代有一个重要的事件,这便是新泰驿道的开通。清初为了加强南北之间的联系,设立了自东南各省至京的驿道,民间俗称“九省御道”。这条驿道便穿经新泰,据《新泰县志·驿站》记载:“按邑在元明时,僻处山径,非孔道也,原无驿路。……国朝(清)定鼎,始于涿州城南,分东西两路,顺治十年()以东南全闽、两浙、吴会、淮扬诸路至京由泰、沂为捷,羊流置驿从此始。……凡輶轩之使,谟猷之告,以及文檄饷课,轮蹄绎络,咸取道焉,而邑遂为冲途矣。”除了九省驿道,新泰西南手车路、西南支路、正南支路、东南支路、东北支路、正北支路等也相继开通。其中正北支路南通费、沂,北通莱、博,亦为要衢。由于交通的畅通,使新泰在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日渐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 喧传一时的康熙、乾隆两位皇帝的南巡,都曾经过新泰。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帝祭泰山后,取道新泰,前往江南,十月十二日曾驻跸于新泰西周村。康熙二十八年(),康熙再度南巡,正月十八日复驻跸新泰苏家庄(均见《康熙起居注》)。在当时宫廷画家所绘《南巡图》长卷第三卷上,便描绘到康熙行经新泰道中的场景。乾隆十六年()乾隆帝南巡回銮,于四月癸未“驻跸公家庄大营,翌日如之”,乙酉“驻跸洪河大营”(均见《清高宗实录》卷三八七)。两地均在新泰境内。乾隆还留下了多首吟咏新泰山川古迹的诗作,据《大清一统志》卷一四二“宫山”条云:“乾隆十六年春,皇上巡幸江浙,经莅山东,有御制《新甫山》诗。”乾隆在经过北师店师旷故里时,又曾赋《师旷村》一诗,抒写了其政治思想(两诗并见《[高宗]御制诗二集》卷二十三)。当时一些名公巨卿、诗人墨客,也都曾经由此道前来新泰,著名学者如吴伟业、王鸿绪、韩菼、唐甄、汪懋麟、王士祯、曹贞吉、屈复、查慎行、洪升、厉鹗、程穆衡、纪昀、阮元、张鉴、孙尔准等,他们在新泰留下的感怀咏叹之作,已成为新泰文化史上的瑰宝。在这条新泰驿道上,还曾留下一些外国友人的足迹,据朝鲜李朝学者朴趾源所撰《书李邦翼事》(《燕岩集》卷六)记载:嘉庆元年(),朝鲜济州人李邦翼遇风漂至澎湖,经由台湾、福建、江浙、山东北返,所过沿途驿站便记有“新泰县”与“杨柳店”(即羊流店)之名。这条驿路的繁盛,由上述资料可见一斑。 清朝入主中原后,采取各种措施,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在地方上,官吏多积极执行朝廷政策。顺治年间,新泰知县卢綋因“時田荒赋重,力请巡按履亩踏丈,更定赋役,民得苏息”,招抚流民数以千计。继任知县杨断芳“开屯规田具据实报”。康熙知县宗之璠莅任值大饥之后,乃“给牛种,轻徭役,民困始苏”。知县吴大梁“勤于劝课,桑麻遍野”。清廷又施行更名田,将明代藩王和大官僚的土地拨给耕者永为世业,新泰的福王赐田因之皆归还民间。耕地面积多有增加,“康熙年间,……共增地一千八十七顷一十七亩三分五毫”(《新泰县志·赋役》)。雍乾时田亩数额也续有增益。乾隆五年()大学士赵国麟奏请弛禁开发煤矿,于是东抚宋定元在泰安、新泰等地设窑开采。(《清史稿·食货志》),泰安之煤窑设于县东南之九龙山(今新泰禹村境),规模较大。同时官府还注重赈济灾荒,康熙四十二年()山东大饥,新泰灾荒更重,康熙帝诏令“官民有情愿效力者,作速遣往山东,不拘银米,同地方官分界赈济”。安徽巡抚李鈵亲赴新泰助赈,计口授食,全活甚众,最后以劳卒于赈所,时人于新泰羊流建李公祠以祀之。又知县吴阶玉时“补兹土,下车之日,輙殄救灾,为吾民谋生活。及岁少稔,则课桑问麻,均徭薄赋”(孙善述《重修三官殿碑》)。在这些正直有为官吏的惨淡经营下,新泰经济得到复苏和发展,时人孙善述记称:“以休养之故,迩来民用恬熙,户饶盖藏,而皇皇然。”(康熙四十七年《重修三官殿碑》)。此外,清廷还在康熙五十一年()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元年()推行地丁合一以减轻贫民负担,至乾隆三十六年(),新泰人口“通计一万五千九百零六丁,视明三百年生齿殆且过之”(《新泰县志·户口》)。至清末更增至“一十三万九千三百八十九口”(《新泰县乡土志·人类》)。 在发展地方经济的同时,卢綋等人也非常注重文化教育的建设,卢綋在任期间,因“邑久乏科第,亲汇诸生课文,教以经史子集”。卢綋、杨继芳还大修庙学,以为诸生讲习之所。宗之璠“康熙己未()知新泰,首注学校,购民舍十余楹为义学,士人宗之”,时人为建讲堂,世称“宗公讲堂”,新泰文风为之一振。康熙末知县王僧慧为政亦“尤重学校”。牟适康熙间为新泰教谕,“虽暑雨祁寒,亦为诸生讲贯不辍”。其后司教陈王前“淹雅博通,勤于启迪”,侯赐乐“倡议重修学宫,教生徒于学舍,一时英俊多出其门”(均见《泰安府志·宦迹》)。除了官学,新泰的书院教育也勃然而兴。宗之璠首创书院于县署东。乾隆年间,知县张师赤以文教自任,于羊公祠设学,延请莱芜学者张湘教授生徒。知县胡叙宁创建“青云书院”,江乾达创“敖山书院”,同治间知县李溱复建“平阳书院”,光绪间兴办新政,新泰知县奎光将诸处书院改建为学堂,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一些知名文人出任新泰地方官吏,也对当地文化发展有所促进,如嘉庆三年()任新泰知县的舒元炜,便是一位以校订舒序本《红楼梦》而享誉文坛的文学名家(参见刘元涛《新泰知县舒元炜与〈红楼梦〉》,载《新泰日报》.10.18)。 卢綋还注重对境内名胜古迹的兴修与保护,他“尝于行省之暇,仰眺宫山,俯临汶水,凭吊师旷、高堂、羊太傅、孙明复之故墟”,凡先贤遗迹,皆为修葺。继任诸令如杨继芳、江乾达等也大都留意文治,对境内胜迹多有修整。康熙元年()漕运总督蔡士英及其子蔡毓华重修敖山三元殿,“庀材鸠工,榱桷一新”。工成,蔡士英亲撰《古敖山今改青云山新修三元殿碑》立石庙前。蔡士英家族为“汉化甚高”的辽东文学世家(参陈寅恪《柳如是别传》~页),其父子相继经营三元殿,使敖山(青云山)之名大著,一时“香火之盛,拟于东海”。《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卷一九二济南府新泰县)中称:“青云山与泰岱、灵岩、五峰、莲花称五山云,祷祀最盛。”新甫(莲花)山上的寺宇,大多亦兴建或重建于这一时期。清末泰安知县毛澂重修和圣墓,用和圣事迹激发乡人的爱国热情,更是为人所津津乐道。清代大兴考据词章之学,考订地志、咏叹山水一时成为社会风气,新甫、徂徕等新泰名山以其丰富的文化史迹,而为当时学者所瞩目,研论记述之作迭见层出,在《泰山纪胜》、《泰山图志》、《泰山道里记》、《泰山述记》、《泰山志》、《岱览》及《燕程日记》、《乡园忆旧录》、《续山东考古录》中都有关于新泰山川的内容,其中尤以唐仲冕《岱览》最为精审与博洽,成为今天研究新甫等山的重要资料。特别是乾隆间学者江凤彝自新甫山下发现《孙夫人碑》后,一时金石学家如阮元、孙星衍、朱文藻、王昶、武亿、冯云鹏等竞相考订,著名画家黄易还以此为题材,创作了一幅《新甫得石图》,更是新泰金石研究的盛事。 清代新泰缺少炳焕青史的名臣,但在文化领域,却出现一些文采风流的学者诗人,为新泰文化史增光溢彩。其中著名者有:张相汉,明末曾官荣河县令,明亡不仕,归隐乡里,著书以终,所著有《四游草》、《新邑志略》等十余种;纪元复,雍正举人,精研经史,著有《四书正解》;牛峡,雍正时学者,曾应知县吴本涵之请,增修县志,未竣,其子基昌复承父业,续辑邑事略二十年,藏于家;牛士瞻,乾隆举人,多识乡故,乾隆《新泰县志》即由其总纂;牛士范,好读书,淹贯经史,以教授为业,泰、肥、沂、蒙间生徒几百余人,曾任青云书院山长,泰安知府朱孝纯曾延请他参加《泰山图志》的撰写;李清濂博稽群籍,训士有法,授教新、蒙、沂、费诸邑,成就甚众,尤工于诗,有《饭山堂诗集》传于世;王青藜,历署邹、滕教谕,有《见山书屋诗集》,其子恩霖、其孙学益亦皆工于吟咏,堪称是文采相继的文学世家;沈毓寅,道光进士,任广西天保县知县,亦工诗。至今泰山普照寺内,还有沈毓寅与王青藜分别撰书的楹联石刻。晚清之郭璞山、冯清宇、卢衍庆等亦皆有文名于乡里。 虽然清代前期号称“康乾盛世”,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仍时常处于尖锐的状态,清初新泰知县卢綋在《丝枲吟》长诗中,通过新泰丝麻从“地利”到“乡害”的变迁,对清廷官吏掠夺蚕民麻农的暴行予以揭露。康熙间新泰教谕孙善述也在《重修三官殿碑》中披露:“兵燹屡警,饥馑频仍,哀鸿雁、嗟硕鼠(指贪官污吏)者遍东土。”骚扰驿站也是长期困绕(扰)新泰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顺治间“沂镇赴省取饷,道经新泰,百姓苦之”。卢綋控于上官,使饷道改于他府,民始得安枕。而后九省御道的开通,为新泰带来生机的同时,也给县民造成沉重的负担,不仅夫马供应繁重,达官贵人更借驰驿之便骚扰民间,敲诈勒索,大为民病,以至乾隆间知县宋焕在《崇庆寺碑记》中发出哀鸣:“邑固硗瘠,加以皇华星使冠盖络绎,夫马之费,供应之需,官于斯者,无可告瘁,……竟不得有大力者一为援手。”因而在新泰,反抗暴政的呐喊接连不断。顺治六年(),“九山巨寇”李梗攻破新泰城,地方官吏望风而逃,由此奏响了清代新泰农民战争的先声。康熙末年,广大贫民为了反对官府的食盐专卖牟取暴利,爆发了由盐贩组织的武装起义,曹龙章、王美公等人聚众徂徕山,曹、王自称“仁义王”、“义勇王”,率部频频出没山中,“率党横行,南北道几梗”,并伏击官商,夺取官盐,徂徕南北,一时成为起义军的天下。著名诗人赵执信过徂徕,曾有“昔为竹溪逸人居,今是绿林豪客穴”的惊叹。康熙六十年()元月,山东巡抚李树德率兵对徂徕义军进行围剿,起义盐徒虽拚死抗争,但众寡不支,不幸失败,曹龙章、王美公被俘后慷慨就义。事后,李树德疏请在徂徕山区驻扎重兵,以防有变。这场起义在徂徕附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盐蝙蝠”的歌谣数百年后仍在新泰传唱不息。 历史进入近代后,捻军数次转战于新泰大地,更在新泰历史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咸丰十年()九月,捻军大部进入新泰,火光烛天,部队东西纵横五十余里,廪生沈庆祜纠集地主武装,于名公洼邀击捻军,被捻军击溃,沈庆祜亦被击毙,捻军取得首攻新泰的辉煌胜利。此后,捻军在同治年间又数次攻入新泰,与清僧格林沁等部激战,前后八年,对清军及新泰地主武装予以沉重打击。在捻军起义的影响下,幅军、白莲教军、刘德沛起义军也都曾活动于新泰。二十世纪初,新泰天灾人祸叠生,疮痍满目,近代作家连梦青所撰《邻女语》说部中,写庚子之年()江苏豪杰金不磨北行过新泰,惟见土阶茅茨,尘沙横飞,赤地如烧,饥民菜色。新泰再次成为绿林丛聚之地。光宣之际,在民族革命的影响下,各支会党武装也曾进军新泰,据光绪三十二年()宗人府主事王宝田等奏称:“娄苦瓜率邳贼二千余人,匿徂徕山、出没新、泰间,与曹(州)贼相应。其出掠皆摇旗鸣鼓,整队而前,所过村镇皆大张伪示,禁淫掠,居人皆奉酒食唯谨。地方官闭城惴惴,恐不自保,以贼不来攻为幸。”宣统三年()五月又奏称:“泰安以徂徕群山为逋逃薮,新泰、莱芜尤被其毒。”(《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可见彼时农民战争之星火,已盛燎于新甫之野。使官府乡绅闻风丧胆。 由于近代列强加剧对中国的侵略,新泰境内的反洋教斗争也此起彼伏。光绪六年(),英国圣公会在新泰建立教堂,受到南王庄乡民的一致抵制,引发了著名的“新泰教案”。在新泰乡民与正直官员李秉衡、徐致愉(戊戌维新领导人徐致靖之弟,时任新泰知县)的密切合作下,终于打破了英人的图谋(据《山东教案史料》)。“新泰教案”作为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势力斗争胜利的光辉一页永载史册。 清代末期,新泰经济仍在艰难环境中发展,其中煤矿业发展较快,孙村、牛家林、沈村等大型煤田相继开采成功。光绪三十二年()周树人(鲁迅)、顾琅所著《中国矿产志》中便对新汶煤田的储藏和开采情况作了载录,其书第五章《山东省矿藏》云:“山东煤矿,德人聂河芬(引者按:今译李希霍芬,F.vonRichthofen)氏检核最详,据所言,则上揭诸地,以沂州……为冠,莱芜次之,新泰尤亚。”又云:“新泰煤田,田在县治北,煤层厚约二尺,凿五十尺至百尺之竖坑取之煤作片状。有光泽,揩之汙指,质复粗疏易碎。当聂氏旅行时,其值每吨十四点零四马克云。”另外盛产于浮邱一带的草帽辫,也在此时远销外洋,获利甚丰,世称“浮邱白”。 随着近代革命高潮的出现,一些新泰爱国志士也走上民族革命的路。新泰北寨人董少羲加入“同盟会”,并曾参加同盟会领导的烟台起义,在辛亥革命的史册上留下新泰志士的踪迹。在民族革命的巨变中,新泰历史也随之翻开了新的一页。 …… 当我们揭开历史的大帷,回溯这一幕幕金戈铁马的风云往事,以及那些名标青史、叱咤风云的乡邦英彦时,使人仿佛感受到风云变幻的时代脉络,遥看到驰骋奔突的银骥长弓,聆听到盛衰兴亡的慷慨悲歌,严峻的历史留给后人以无穷的遐思与启迪。 新泰范整合原创,未经授权严禁公号转载 赞赏 长按北京白癜风治疗好招聘社群营销
|
当前位置: 饶阳县 >新泰的历史,你知道吗史上最全版本
时间:2017-12-1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河北发布高考报名须知如何申请加分更多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
- 热点内容
-
- 没有热点文章
- 推荐文章
-
- 没有推荐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