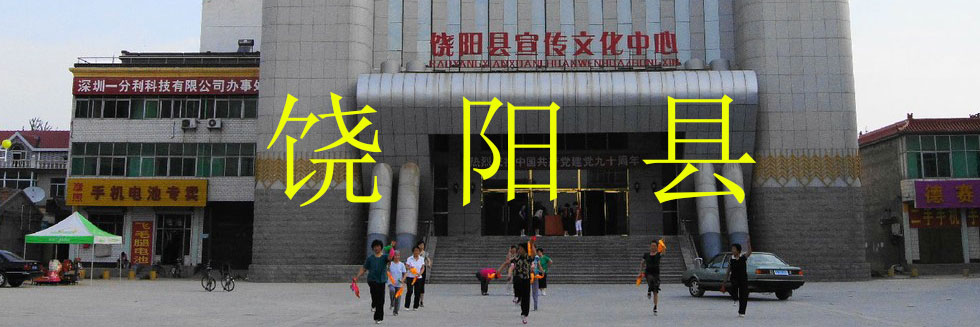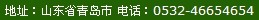|
说纪铁榜是饶阳的历史专家,绝非调侃之言。 老纪是六十年代初考入南开历史专系,毕业时分到新华总社,后为照顾老母弱妻,又自动调回县里,真所谓“龙游浅水”了。所幸的是,回县后他在政府部门一直从事自己热爱的专业,编写县志、地名志和人物传,取得骄人成绩,退休前已被评为编审职称,并被省、市各级聘为评委会的委员。 老纪最大的特点是只做学问,不计名利。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一般最看重和计较的是级别和职务,但他的脑子里只有工作和任务,却从没有争过什么。县里的县志办和地名办原来是一套人马,两个牌子,老纪一直是实际负责者和具体执笔者,但这个机构一直隶属县政府办公室代管,有时还要由政府办的人兼职,老纪就只能一直挂个“副”字。一九八八年,正是县志收集资料,突击整理大事记和部分专业志的关键时刻,那时正好由我兼任主任,把任务和老纪一说,他就昼夜加班干起来,两眼成天熬的通红。手指尖也被烟油子薰得焦黄。有一次市史志办要组织各县人员到桂林旅游,我找财政要了经费,就催他去旅游一次,这对别人是求之不得的,但他却说:“现在正是磨扇压手的时候,我不能耽误。”我说:“你出去散散心,放松一下,不然身体会累垮的。”他仍旧毫不含糊地一口回绝,还非坚持要我去,我那时在政府管综合材料,也抽不出时间,就劝他说:“修志这个大工程,不在乎十天半月,你要不去经费不白拨了?”他想想说:“这活儿不能再耽误了,要有钱,你看能不能给我买成资料书,我现在买书已花了好几千元,很多东西还是查不到。”我被他的敬业精神深深感动,自然是同意了。那一年多老纪就写出了大事记和二十五个专业志,全部打印成册,为县志成书打下了基础。同时,还为河北出版的大型书籍《燕赵游子录》写了十几篇饶阳重要人物的传记,是衡水各市县中的收录最多的。 俗话说,尺有所长,寸有所短。老纪这人工作玩命,认真负责,令人十分敬佩,但个人生活却非常马虎潦草,毫不在意,甚至在一些日常问题上常常表现的束手无策,似乎像是笑话。那年他相濡以沫的老伴因病去世,因当时县里尚未推行火化,没有丧葬车辆,拉回原籍葬埋需要找车,但老纪却不知到哪里去找。他平时埋头书斋,足不出户,一心著述,无意交往,不仅和县直单位缺乏联系,就是乡里乡亲也极少走动,所以一碰到这种事情自然是六神无主。那天我赶到时他正急得掉泪,见我一去,他好像有了一点主心骨,嗫嚅地说:“这种事,反正不能用政府的小车吧!”我一边安慰他,一边叫管后勤的同志在油棉厂找了一辆客货。这在别人是举手之劳的事,于他却是很大的难题。也许是潜心做学问钻得太深,其它事根本没有考虑过的原因吧。事后多年他还常说:“要不是你们,我知道往谁找车呢?我怎么知道哪儿有这种车呢?”前几天,他又给我打电话,说和我有事相商,我表示什么时候都行,他又说:“我现在住五楼,腿脚不好,你要到我这里来!”我于是就马上赶去。见我去了,他神情有些激动,就想给我倒杯水,但找了半天却找不出一个干净的茶杯,后来爽利拿出一个吃饭的花瓷碗,给我倒了满满一碗白水,说:“你看,茶叶我也找不到。”看的出,他虽退休已近十年,但生活还是那样没有规律,只是烟照旧抽的很凶,一支接着一支。一边抽还直劲往我手上塞。看着他的样子,我不禁想起了把手表当鸡蛋放在锅里煮的牛顿,叫人心生敬佩,而又有些不可理喻。虽然他在生活上不修边幅,丢三拉四,但谈起饶阳历史事件和人物却博闻强记,引经据典,话语滔滔,令人赞叹。 原来退休十年他并没有闲着,仍旧在家写他的史志资料。他说已经写了三本饶阳的文史资料,尤其是对一百九十多个村的资料都重新整理了一遍,还在县电视台开了讲座,他找我的意思就是考虑以后饶阳史料工作的传承问题。他说上几天政府史志办一个年轻人来找资料,他没舍得出手,问我的意见,我说:“你应该搞一下传帮带,把知识和学问传下去。”正好我和那个年轻人也熟,就叫出来请他们共同吃了一顿饭。在酒桌上我和那个年轻同志说:“治史难,做人更难,我们都要向老纪同志学习呀!”那个年轻同志自是频频点头。 鲁迅先生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即使那些等于为帝王将相做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他们是中国的脊梁。”老纪不正是那种“埋头苦干”的人吗?说实话,我多年混迹职场,看惯了那些蝇营狗苟,投机钻营,争名夺利,尔虞我诈,但像老纪这样为人处世的实属一个特例,他无论在职还是退离,脑子里都是想的饶阳及这个地方的历史,没有为自己的待遇分过心,说过话,甚至连想都没想过,这种干部现在还有多少呢? 何同桂扫一扫下载订阅号助手,用手机发文章赞赏 长按白癜风的治疗费用白癜风的治疗费用
|
当前位置: 饶阳县 >饶阳这个历史学家一门心思钻研县城史
时间:2019/12/26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咱饶阳越来越有国际范了,中外雕塑艺术家都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
- 热点内容
-
- 没有热点文章
- 推荐文章
-
- 没有推荐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