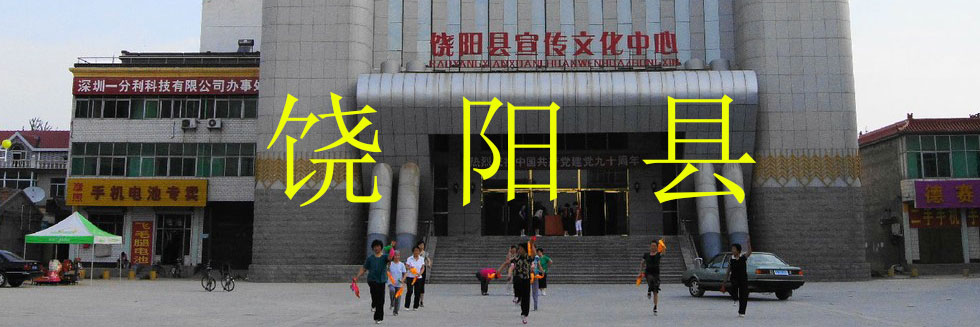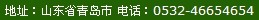|
我出生于年的河北献县,从那时到年的夏天,一直生活在比较纯粹的方言环境中。 在最初的记忆片段中(如与家人一起拔野菜、与同村人一起捡花生等),语言的角色是很模糊的或是根本没有,直到有一次,大约在年前后,我听到家人聚在一起商讨一件事,一个人不停地愤愤地说“早晚如何如何,早晚如何如何”,这句话让我很迷惑,本地话中“早晚”与“凿碗”的发音相同,我那时不知道有“早晚”这个词,就以为他说的是“凿碗”,疑惑他为什么要去“凿碗”,现在推想应该是“早晚”。 我年开始在村里的小学上学,老师和同学在所有场合都说方言,但当年从外地转来了一个女同学,当时约7岁,这名女同学原为本村人,三岁时到吉林省生活,后又转回本村,这名女同学在读书时说的是普通话,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普通话并意识到那是一种与自己说的话差别很大的东西,我和其他同学一样,感到这种腔调很“洋”,但并无意愿去模仿,那名女同学也大约不到一年的时间就不再说普通话了。 年夏天,我开始看电视,对电视中的普通话和自己说的话的区别没任何感觉。但那时注意到一个现象:本村人对所有有别于自己的方言以及普通话都形容为“侉”,只要本地人之间有人用非本地话说话了,一定会遭到嘲笑。有一个例外是,村里有一个老太太,说的是外地口音,但村里人不说她说的话“侉”,而说她“呛(上声)”,并给她起了外号“呛子”,在我记忆中没有别的人被称为“呛”了,这个老太太在我知道调查方言时早已去世了,根据记忆中的印象,她的方言应该属于离献县较远的河北山东交界处的方言。 我年到年在离村子约6公里的乡政府驻地上初中,老师和同学在所有场合都说方言,但是,我那时已经注意到两种话的存在;献县话和河间话。有的有的邻村同学说的话可归入河间话范畴。 我第一次短期到城市去也是在这一时期的年,在石家庄市的舅舅家待了十来天,在舅舅家的时候,舅舅虽是献县人但说普通话,舅妈家是旗人,本人说北京土话,我则仍说自己的方言与之交流,我第一次感觉说话很别扭,我感到自己能说普通话,但是怯于出口。不过还是有一个机会让我第一次说了普通话:我在书店买书时因为不懂购买规则,把书带出了指定区域,结果被管理人员扣留了,我用自己的方言争辩了几句,对方不理睬,我羞恼之下,含着泪水恨恨地用普通话说了一句“这就是你们石家庄人!”那管理员得意道:“就是,怎么着吧?”我从那一刻起,知道自己是能说普通话的,只不过现在已无从判断那时的发音状况。 我年到年在献县县城上高中,注意到除献县城关话、河间话以外的另外几种本地方言,可粗分为饶阳话、郭庄话和高官话三种,这些话相互之间的区别明显。老师在授课时有些用普通话,有些用各自说的本地方言,但在课下说话时都用方言,而且老师和同学之间各自说自己的方言,没有人模仿对方的方言,也从不用普通话作为交流工具。 我年到年到位于河北保定市区东北郊的河北大学上学,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入学的那一刻就开始和同学说普通话,没有任何过渡。在上学过程中自己掌握了普通话和保定话的对应规则,能按照规则来说保定话,但几乎从来不说。在年的时候,我回献县一中看望复读的同学,同学们说我说的话变了,我很惊讶,因为自己没有察觉,依照现有的语言学知识分析,那些同学把更多文化词汇的使用也看做是换了方言。在一次现代汉语课上,老师带领同学做简单的普通话测试,我说的普通话被认为是带有方言色彩,但当时还说不清这种色彩的具体表现。 年至年,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系统学习语言学知识,开始回顾自己的说话史并记录自己母语方言的词汇和音系。 年至现在,我在河北大学任教,在外都说普通话,在家里说方言(因家人都和我方言相同,妻子就是当年那个曾让我第一次听到普通话的小学女同学,她的普通话水平反倒低于我了),并且,不论在哪里见到献县老乡,不管他说的献县方言和我是不是一个类型,我都会与其说我自己的母方言,对方也会说他自己的母方言,我在做这种转换时不感到有困难。 年1月我的儿子出生,我在教他说话时常犹豫应该教他方言还是普通话,结果便成了一种混杂的状态,即有时用方言有时用普通话,我妻子也是这样。结果跟预期的一样:儿子最终的学会的是普通话,并且不会说献县话。 长按下面的治疗白癜风药北京治疗最好白癜风的医院
|
当前位置: 饶阳县 >我的说话史语言与生活
时间:2018/3/21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说说咱们深州方言,看看是不是这么个情夸儿
- 下一篇文章: 要闻热烈欢迎市政府和市经合局领导莅临我校
- 热点内容
-
- 没有热点文章
- 推荐文章
-
- 没有推荐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