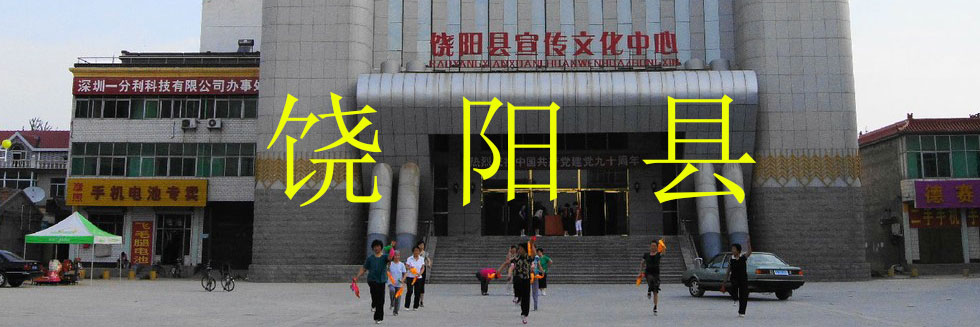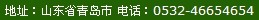|
我心里有棵绒花树,多少年来一直记着,想来总那么清晰,不仅喜欢那绿绿的,成串的小叶子,还有那针刺般毛绒绒的,粉红色的花。 但真正叫我刻骨铭心的是,就在那棵绒花树下,我认识了师姐。 说来早了,我年轻的时候,至今已有36年了。那时我考上了冀县师范,学校的前身是“直隶六师”,“直隶”是哪儿?现在的京津冀,再加上辽宁、山东、河南各一部分,前清时期“直隶总督”那可是朝廷重臣。 我们那年特别,5月考试,6月入学。记得是中午,天气很热。 师姐在报到处负责办理登记手续。她先收了我的准考证,还有户口关系、粮食关系,末了师姐给我一沓饭票,她那纤纤素手轻轻一扬,指了一下东面礼堂的门,说:“去那儿吃饭吧。” 真是无巧不成书,我转身时不小心打翻了她面前的杯子,水漫在桌面上,慢慢蠕动着,师姐忙撂下手里的活儿,五指并拢,铺平,把水轻轻抹下去。我凝神看着姐姐的手指,白而细长。 把那水抹掉后,师姐双手对准我轻轻一弹,几滴水珠便粘在我的脸上,那水温温的,不凉,我一激灵,师姐笑笑说:“小师弟,怎么这么冒冒失失的?”我脸发热,虽看不见自己的脸,准是腾的就红了。 我定神看了师姐的模样:她身条匀称,着一件白底小粉花连衣裙,齐耳的短发,面庞白皙红润,双眼皮,带着天然的笑意,尤其是眨眼的时候,很是妩媚。我看见她白皙的项上挂着一个粉红色的纸牌牌,工作人员:秦绒。所在班级:46。 我惊异于师姐把水弹在我的脸上,因为我家从小就几个弟兄,没有姐妹,平时对异性怀有神秘感。而师姐第一次见面就像亲姐姐一样,不经意间释放着女性的温柔,让我心里有异样的感觉在萌动。我更惊异于当时的环境,可谓天人树合一,高天蓝蓝的,飘着白云,报到处的上空,是一颗绒花树,也就是合欢花,枝叶繁茂舒展,浓阴如盖,枝杪缀满一簇簇毛绒绒,针刺状的,红粉相间的花。 对于绒花,资料是这样介绍的:绒花(合欢的别名),“合欢为落叶乔木,树冠宽展,二回奇数羽状复叶互生,头状花序呈伞房状,簇生于叶腋或枝梢,花萼及瓣黄绿色,多数粉红色花丝聚集成绒球状。” 越看越觉得惊异:“咦?我怎的会在这样神话般的境界里遇到了师姐?” 入学后的最初几天,心里总在想着师姐的举动和话语。 渐渐我悟了:师姐就是我生命中的贵人。当我从苦海般的煎熬中爬出来,到冀县师范报到,那报到处就是我渴望的幸福的彼岸。或许姐姐就是冥冥之中接我出苦海的菩萨。她的微笑,弹水,嗔怪,无不有着生命的内涵。弹水,是让我清醒起来,嗔怪我“冒失”,实属指点迷津,指引我修身的方向。师姐告诉我,一个男人应当沉静稳重,冒冒失失、慌慌张张能成何事? 正式上课之后,几乎就没见着师姐。心思闲暇时,有时就想她,偶尔在餐厅远远的见到了她,虽然不能说一句话,但心里也能高兴一阵子。 冀县师范后面,有一条东西方向的古城墙,傍晚同学们常去那儿玩儿,那地方很美,很雅,很沧桑,在城墙上漫步,着实是一种享受,那一年四季的景色都能见到,永远忘不掉的是那簇簇野花,丛丛绿草,片片芦苇,以及冬日的雪光。 那是一个秋日,大概是中秋节以后了。西天的太阳红红的,秋风有些凉爽,但还未萧瑟,吹得芦苇起起伏伏,唰唰的响。我在墙上走着,就看见师姐在一个矮矮的砖跺子上坐着,双手抱着双膝,望着墙北边的芦苇,像在想什么心事似的。 我走到师姐身边,躬身冲她微笑着:“师姐,累了吗?歇会儿?” “是啊,我在墙上走了两个来回啦。”她说,顺手拍了拍土,站了起来。 俺姐弟俩就这样窃窃私语的聊着,其他散步的同学或男或女,仨一群俩一伙的从我们身边走过,有的还投来疑惑的目光,因为我在那批学生里年龄是比较大的。当时大部分学生都是应届高中毕业生,而一小部分是社会青年,而我就是这一小部分中的一员,我是以代课教师的身份考上冀师的。我理解师弟师妹疑惑的目光,他们似乎在问我们:你们在干吗呢?谈对象吗?其实真的没有,在我的心里,秦绒永远是我的师姐,我尊重她,崇敬她,不敢想别的,我觉得我配不上师姐的灵秀,我不想做望天的蟾蜍。 和师姐聊了一会儿,才知道她就是当地的,冀州人,老家就在“千顷洼”,现在人们叫“衡水湖”的边上,那个村子叫水蓬塘。 师姐的父亲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原来在教育科学研究院工作,“文革”时受冲击回到了老家,也就是那个叫水蓬塘的村子,在师姐12岁时就因病去世了。这样,就只剩下师姐和母亲相依为命,按师姐的说法,日子过得很清苦。 和师姐聊天,知道她童年的苦,心里想哭。我垂着眼皮,眼角似有湿湿的东西浸出来。可师姐依然那么阳光。 不经意的瞭望时,看见城墙北边的不远处,有一大片的高粱和玉米都熟了,猛然心思飞到了家里,家里人正忙活收秋的吧,这时又忙又累的。我问起了师姐:“家里有活儿干吗?” 她也似有所悟:“还真的有,我这两天就想回去呢,有点玉米花生该收了。” 我问:“怎么还种地呢?” 师姐说:“按说俺家是没有地的,俺们是城镇户口,不是农业户口,分地那会儿就代种了一块儿,每年就种点小麦,玉米,花生,还好管理。” 我问:“那这几年你们是怎么过来的?” 师姐说:“都是俺妈干活,有时就叫人帮忙。” 师姐哪里知道,她这句话像一条闪电,霎时照亮了我的心灵,我说:“你哪天回家?我找几个人和你回去收秋吧?” 经过几番推辞,我和师姐还是说定了,星期天我找四个人,连我五个人,加上秦绒一共是六个人,去给她家收秋。 因为那时还是单休日,学校就星期日一天不上课,自由活动。 既然说好了去给她家收秋,我心里很兴奋,很高兴,也就利用星期六的晚上,找了三个师弟和一个师妹,在冀州老城邮局边上一个小餐馆,喝了一场小酒。平时我们在学校早晚的主食就是窝头咸菜和稀粥,中午有个馒头吃,还觉得好吃得不行。可我请客了,叫弟兄们吃啥?下酒菜记得有一盘花生米,一盘香肠,一盘豆腐皮,一盘炒茄丝。酒是一瓶衡水老白干,那个小师妹只喝了几口茶水,主食就是每人一盘焖饼。吃完饭时,我就大声说:“明天咱得受些累,我揽的活儿,给师姐收秋去,一天干完“。 星期天,天刚亮,大地洒满霞光,我们几个就骑着自己借的自行车,到了水蓬塘。 师姐的家,就在千顷洼的边上,出门就能看到那水面波光粼粼,空气里弥漫着水气,千顷洼的水边上,有簇簇丛生的芦苇,有摇曳生姿的水蓬花。她家的房子从外边看与普通的民房没什么两样,可屋里却是别有洞天。刚进屋门,仰头就见三扇屏,中间的画面是一株工笔重彩的绒花树,这使我觉得太别致了,我从没见过有谁家有这样的画。而绒花树的两边是一副对子: 删繁就简三秋树, 领异标新二月花。 屋内有书柜立着,弥漫着文化气息,师姐的母亲是有着文化内涵的人。我们喊了几声伯母,就张罗着收秋的活儿。 师姐那点活儿是:一亩半的玉米,用小板镐刨下来,玉米掰清楚,拉回家;半亩的花生,用大镐刨下来,落在地里的花生要拾清楚,拉回家。 我是领头者,我算计着,我在生产队干过活儿,知道帮着师姐做这点事,我自己,还有我请来的师弟师妹需要流多少汗水,但我不觉得苦和累。 那天干完活儿,我们六个人一起回学校。已经是晚上了,有月亮,有位师弟还扯着嗓子喊起了京剧《沙家浜》的唱段: 月照征途 风送爽, 穿过了, 山和水, 沉睡的村庄…… 然后就飘起一阵爽朗的笑声,我深深记得,师姐的笑声融化在了月夜里,也永远融化在我的心里。 可是,帮师姐收秋后那个秋天,师姐就毕业了。 一晃,36年过去了。我再也没见过师姐的面。虽然常常思念她,祈祷她,可就是见不着,听说她随了军,丈夫在重庆服役。 这些年我见过一些自己喜欢的树,如塔松,海棠,玉兰,菩提,等等,但都是过目而忘。却只有冀师的绒花树,永远牵着我的情思。无论在哪儿见到绒花树,瞬时就会想起冀师,想起冀师的绒花树,想起古城墙,想起千倾洼的芦苇,想起和师姐这段情缘。师姐去了远方,但阻挡不了我的思念和祝福飞越山高水长。似乎时光越是久远,这种情感愈是浓烈。还是用那首古老的诗篇,来表达我的情感: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甜蜜的回忆中有着一丝涩涩的酸楚,一篇优美的散文。编者:映雪松按。) 附记:我是冀县师范79级1班毕业生,我报到的真正时间是年11月3日,属深秋,霜降节。当时我报到时接待我的师兄师姐,我依稀还记得,只是这些年倏忽就老了,师兄师姐都没见过面,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但是对于她们的情感却没一丝的减退,倒是随着岁月的久远,那种情感便愈发的浓烈。写这篇四不像的文章,算是对这种情感的记录吧。 文中人名为化名,敬请见谅。 作 者 简 介 作者简介:王永康,男,年生,饶阳县人,就读于河北冀师级1班。曾任教师,后转入政法系统,在饶阳县法院工作,现已退休。 冀师校友美文推荐 父亲节特刊:幸福之旅 初恋 (原创)冀师有乔木 以校友的名义——北京治疗白癜风术要多少钱专业治白癜风医院
|
时间:2017/10/19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咱邢台的这2样东西国家明确要保护啦即便
- 下一篇文章: 饶阳团县委为建设美丽家园助力加油
- 热点内容
-
- 没有热点文章
- 推荐文章
-
- 没有推荐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