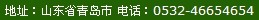|
年,在北京家中。左起:母亲陈布文、张郎郎、父亲张仃。 人,是有预感的。在饶阳县的时候,有一天半夜我从噩梦中惊醒。醒来以后,梦中的画面还在眼前挥之不去。我梦见和许多朋友,坐着大卡车在黑雾里行进,感觉还是在被押送中,但是四周见不到警察。那卡车就开到一条奇怪的街道上,街道两旁有无数的小巷。我们的卡车开到每个小巷前都停一下,为的是看清小巷口悬挂着的巨大白幡。那些白幡上,有许多黑灰色的影像,如魑如魅,似乎都是注定的鬼魂。我心里明白,这些都是即将执行死刑的人们。怎么会这样呢?突然,我明白了,这辆卡车里的人,现在还都活蹦乱跳,我们也将进入某个同样的小巷,我们也将化为鬼魅似的影像……这时候,我一身冷汗醒来了。当时还庆幸,还好不过是个噩梦而已。 如今,这个噩梦几乎是不差毫厘地再现了出来,我想,那一个个的小巷就是一批批被执行的人,我们就是急匆匆的后来者,而判处我们死刑的资料,就是那些巨大的白幡。 进了死刑号以后,每天即使入睡也绝不香甜。每时每刻一种尖锐的肉体痛苦无法停止,如刀割心头。那时的噩梦已经没有了以前的那种复杂情节和过程,老是梦见自己漂浮在漆黑的地铁里,地铁里似乎发生过地震,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钢铁框架、水泥碎块、石柱木梁,我就被挤在一个狭小的夹缝中,冰冷的地下水一点点地漫上来,自己的鼻子紧贴在地铁的穹顶上,清楚地知道很快就会窒息,没有任何逃脱的可能性,只在等那冰水最后的淹没。 每天在醒来的前一秒钟,似乎心里快乐了一下,哦,原来是梦。可是立刻又在尖锐的痛苦中想到,原来我还没死,可是我就在死刑程序中。人生,多数时间都是非常单调和无趣,只是在无边苦海中挣扎而已。没有什么值得你去回忆,只有两种状态,让你难忘:要么你在苦海里急速下降,随时会被溺毙;要么你从海底迅速上升,将吸到新鲜空气,会看到蓝天白云和阳光,还有你苦海的地平线。在死刑号的日日夜夜,我都被压在铅一般沉重的水底,在终极前苟延残喘。 年7月,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的《一个文人的从心童画》张郎郎个人画展上,左起:张郎郎、狱友范铸明。 那些日子里,每天都要进行两场批斗。有一次,在重型机械厂礼堂的后台等候出场的时候。孙秀珍进来了,她和我打了个照面。她已然不像在学习班那样——仪态万千,甚至还不如在冀县上车的时候。她一副心如止水的模样,看到我时微微一愣,眼圈儿顿时就红了。 在队长的命令之下,我们俩都坐在地上。 她肩膀抽搐着哭了,女队长轻轻地踢了踢她,说:“哭什么哭!今儿又怎么了?你不是挺横的吗?”她似乎无知无觉,自己继续啜泣。 多年以后,我遇见了她当年的同屋——北京医学院的学生李世佺。她告诉我,孙秀珍的家是个小康人家,有姐妹三人,年前父亲是个小业主,很早就过世了。三个姑娘都心灵手巧,特别能干。 老二孙秀珍骨子里是个爱情至上的弱女子,却也是典型的“红颜薄命”。她命苦,先嫁给了一个每天下班后得先到母亲和大姐那儿去报到的卑微男士,她咬牙过着乏味的日子。她是从北京医士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挑花厂当厂医的,那是一个集体所有制的小厂,没想到在那儿遇见了复员回来的厂医田树云。老田顿时对她展开了疯狂的追求,海誓山盟一定要娶她。孙秀珍后来对李世佺说,女人一辈子就是在等着被人全身心地爱。 为了田树云,孙秀珍毅然决然地向丈夫提出离婚,这下她周围一下炸开锅了,从里到外骂声四起,但最后居然被她离成了婚。可是,田树云这时候却没接她这个茬儿,竟和另外一个出身好的姑娘结婚了。孙秀珍这时候才知道,爱情再浪漫也抵不上现实的分量。 “文革”爆发了,田树云在厂里的日子也不好过。也许家里的日子渐渐没意思了,他又卷土重来,告诉孙秀珍自己真正爱的人还是她,在现实社会中,他没钱没势也没有前途,他们的爱情是没有结果的,他还说,他已经和苏联联系好了,只要孙秀珍帮他一把,定期把他写的信件投入指定的汽车里,建功立业以后,他们就可以比翼齐飞,一起到苏联去过神仙日子。 孙秀珍压根儿对政治一无所知,也从来不关心。这时候,她对田树云的感情也半信半疑,可是看他一脸真诚,孙秀珍决定赌一把,万一是真的呢?就这样,她变成了这个案件的胁从犯。 进了监狱以后,她一直和李世佺同学及吴世良女士同屋。经过多少次提讯,她才知道田树云讲的故事不过是天方夜谭,是在利用她对爱的向往。在监号里,她心灰意冷、万念俱灰,所以,平时温柔可爱的她,一旦面对刁难她的女队长,顿时横眉立目、异常勇猛。难怪吴世良女士说:“小孙,天生一个美人坯子,乌黑的头发,水汪汪的大眼,窈窕的身材……没想到,面对强势从不低头。她外表是美貂蝉,骨子里却是猛张飞。” 李世佺告诉我,其实听吴世良女士这样说,她也不以为然。那时孙秀珍只是被逼到那份儿上了。她原本一心就想当一个小女人,等待有人来疼爱,可是命运捉弄了她,让她面对铁窗,她只能刚烈。在学习班里,我们之间交换的书信,我写的那些类似法国诗人沙尔·波德莱尔的忧伤情书,给了孙秀珍瞬间的喜悦和安慰。或许,那只是她暗夜中的一缕微光。我写的那些信,她只给李世佺一个人看过。 一次她们嬉笑着看完以后,李世佺说:“他这么动心动肺地喜欢你,将来出去以后,没准你们俩还真有戏。”孙秀珍苦笑着说:“我已经是残花败柳了,而他不过是个学生,是个孩子。他哪儿知道我呀,等他了解我了,还有什么戏?我们只有此时此刻,哪儿有什么将来。” 孙秀珍说的也对,在那个时刻,外面的世界和我们无关,我们已经属于了另类的人群。以前喜欢我或者我喜欢的女孩子,我那时候已然不抱任何幻想,知道绝对不会有什么“将来”了。孙秀珍——“库里娃”,就是我黑狱中娇柔的花朵。 那天哭泣的孙秀珍就坐在我旁边,几天的批斗之后,我们都已经是蓬头垢面,手腕脚踝全都血了呼啦。她嚶嚶地哭着,似乎是在回答队长们,其实我知道她是在对我说:“我这辈子,过得太不值了。来都不知道为什么来,走也不知道为什么走。刚想好好活下去,才发现再没有这个机会了。” 女队长厉声地呵斥孙秀珍:“别胡说八道,宣判你了吗?你只有老老实实地接受批判,才有出路。”她停止了呜咽,说:“什么出路不出路,我清楚得很。我不是和你们过不去,只是为自己的这辈子伤心。” 这场批斗会我们俩是主角,起立准备上场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对视了一下,我努力对她微笑了一下,微微地点了点头。孙秀珍的一双泪眼望着我,依然那么楚楚动人。我想,她也是在为我伤心,她读懂了我。 张郎郎作品《青山微风过》 布面丙烯综合材料×75 那时候,我们每天至少出去被批斗两场。在这几十场的批斗会里,有两场是我永生难忘的。 一次是,我被拉回自己的母校——中央美术学院,把我拉回那个熟悉的舞台,我曾经在这个舞台上扮演过古希腊的寓言家——伊索,在全剧结束的时候,我站在这个舞台上,这样高呼过:“人们啊,听听伊索最后的一个寓言,狼问狗:‘是谁把你喂得这么肥胖?’狗说:‘我的主人!’狼高喊道:‘我与其饿死,也不戴上那条锁链。’人们啊,让我作为一个自由人而死去吧!”没想到今天我居然会回到这里,重复着千年前同样的故事。 那天,现场激动地发言,要求枪毙我的老师、同学,并没让我伤心。我知道,他们一定是迫不得已,他们只是期望自己能好好活下去。人们在生死这个关口,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我想,作为演员,我比他们演得更为真切。 另一次,我被拉到父亲任教的学校——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同时他们把我父亲张仃和我年幼的弟弟寥寥押在台下陪斗。那天,我看到老爸的头发全都白了。他为我如此担忧,更让我难过。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当老爸得知我被判处死刑后,一夜之间白了头。 我看到幼小的弟弟长高了。他那么无助、瘦弱,真希望他能走出我这晦气的阴影。我期望他们能理解我,可是我却无法说出一个字。 为了让父亲和弟弟知道我依然身心健全,在走入会场的时候,我放稳了自己的脚步,铿锵有力地蹚着我的重镣。这道具很质朴,你蹚好了,那声响相当沉着。我老爸和弱弟也都不含糊,他们和我一样平静地面对群众的疯狂,淡然处之就是刚强的心态。 当批斗者第一次喊“现行反革命分子张郎郎”的时候,中间的警察就扯住我的头发往后一拉,让我在群众面前亮相。从第一次批斗开始,我就知道了这个程序。从第二次开始,每当我将被动亮相的时候,我已经准备好了一个平和、友善的面孔。我想让人们知道,我没有被粉碎,也没有被打垮,我不是你们心中的假想敌。这次,我给这场批斗也准备好了一个微笑的亮相,参加过这个批斗会的人,应该是记得的。 很久以后,我听说在同一天,居委会主任和两个警察来到我们家,他们要找我妈妈谈谈。他们知道我家孩子多,万一有人想不开,会有更严重的后果,所以我妈妈得首先想得开。妈妈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望着远方。警察走上前来,说:“你孩子犯了大事了,又赶上点儿了,你可得想开了。这会儿谁都没办法。你们家的人,可别胡思乱想,别出了岔子。”妈妈平静地说:“我小时听说过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们,因为写东西被判处死刑,那时候他们就是我心中真正的英雄。没想到我儿子也成了这样的人。我没什么想不开的,我为他感到骄傲。”主任连忙对警察说,老太太疯了,快走,快走。 张郎郎作品《慨当以慷》 布面丙烯综合材料×75 警察为了赶时间,往往就把我们直接扔到卡车的车厢里。我们的脸就被车厢底部的铁皮蹭出血道子。我的手腕和脚踝都被镣铐磨得鲜血淋漓,只得撕开自己的衬衣,嘬着牙花子,慢慢绑裹自己的伤口。这哪儿是要处死顶天立地的野狼呢,这就是想让你像条癞皮狗一样被折磨。这时候,我才明白了什么是“只求速死“的心态。 当然,什么事都有例外。有一天,我们被拉出死牢,没想到天气居然开始转暖,天也晴了。也许是天气的关系,队长们的脾气也见好转,也有点儿耐心法儿了。这天,他们没把我们扔到车厢里,居然还搬了一把椅子,放在卡车的旁边。两个警察把我一举,我就站到椅子上了。车上的警察又拉了我一把,我提着脚镣轻轻一跃就上了车。卡车两边坐满了警察,我就坐在中间的地下。这时侯我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也被架上车来,那就是我心中的“库里娃“——孙秀珍。她今天的状态好多了,大概她也想开了。 孙秀珍似乎好好地梳洗打扮了一番,她比在学习班的时候消瘦了不少,却更显清秀了。原来这辆大卡车只拉我们两个人。我想,大概今儿就是我们的大限了。最后的日子,能有一个心仪的伴侣,还不错嘛! 队长叫孙秀珍和我背对背地坐下,临坐下来时,她假装看落座的地方,在百分之一秒中,我们交换了深深的一瞥。不知怎的,我心里那个微小的金色火苗,瞬间被她的目光催化成了熊熊烈焰。 我穿着一件蓝色的棉大衣,孙秀珍穿着一件碎花的小棉袄,我们温柔地靠在了一起。周围的警察互相打招呼,开着玩笑。他们和我们是两类人。这会儿,他们眼里没有我们,我们也对他们视而不见。此刻我心里只有她——优雅的“库里娃”。车开动起来了,我用自己的肩胛骨紧紧地靠着她,她也在尽量地靠近我,我们的生物电和热量通过后背暖暖地交换着。在那段时间里,我心里慨叹不已,没想到在死刑号,我还能和她有一次真正的零距离接触。两个死囚就这样紧靠在一起,在那些日子里,这是唯一的甜蜜。 原来,我们是被拉到官园体育场去参加批判大会,我们俩是唱头牌的。同场有一个师大女附中的孩子叫文佳,她和北医的学生李世佺是一样的案子,她们都是“反动日记犯”。后来,听说她们俩都判了十多年徒刑,比我们强点儿,我们都已经是死囚了。大概那几批死囚中也就我们俩,还在坚持着最后的浪漫。 晚上,我们在回死牢的路上,两人还是背靠背地坐在车厢的地板上。我们运气不错,回来的车是个大轿车。穿过长安街的时候,辉煌的灯火穿过车窗闪烁在车厢里,投下斑斑光影,这给我们最后的浪漫抹上了几道光彩。我们一会儿轻柔一会儿紧密地靠在一起,我心想,要是天天能这样出来批斗也就值了。但我心里明白,没那么多时间了,也就这几天了。 第二天(年3月5日)早上大约四点多钟,我听见许多卡车开到我们的墙外。五点钟就让我们全都起床了,每个人发了两个窝头、一块咸菜,没有菜汤,也不给水。我知道,去刑场前还得参加一次公判大会——最后的审判,所以不让我们饮用任何液体。六点钟左右开始叫人,也是隔几分钟叫一个。我们安静地坐在炕箱上,等待着最后的点名。我听见,他们叫了遇罗克、田树云、孙秀珍、王文满、宋惠民、索家麟、王涛、沈元等。 这些都是我认识的,还有我不太认识的北大毕业生顾文选等。我听得见,每个人都是蹚着脚镣走到小院里,然后“轰隆”一声就被撂倒,随着就听见囚犯短暂的挣扎声,口中呜呜地哼几声就安静了下来,然后被架上汽车,这辆车开走,另一辆汽车开始缓缓开来······ 我等着,等着,等到最后,听见他们竟然把死刑号的筒道大门都给关上了。这次没有我?!是的,没有我,也没有我的同案。 筒道里死一样的寂静。那天,他们都没有回来。孙秀珍——我的“库里娃”,她真的就这么走了?我不知道。虽然我还苟活着,却从此再也见不到她了······ 本文选自张郎郎文集《郎郎说事儿》 艺术家张郎郎简介 张郎郎,年11月7日年出生于延安,著名画家、美术设计家、艺术评论家、诗人、作家、文化学者、教育家。 其父张仃先生是共和国国徽主要设计者、开国大典的设计人、绘画大师。母亲陈布文先生是作家、教师,曾任李立三、周恩来的机要秘书,也是王蒙的小说《女神》的原型。父母分别从艺术上和文学上给予了张郎郎很大的影响。 年,张郎郎和一些同学、朋友们热衷文学和艺术,经常聚在一起看书、写诗、画画,形成了一个文学沙龙“太阳纵队”,张郎郎成为文学沙龙的精神领袖。 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美术理论系。 同年受父亲和丁绍光装饰绘画的影响创作了一批画作,装订在一起,起名为《随梦录》。 这段时期张郎郎写了长诗《燃烧的心》、独幕剧《对话》、电影剧本《孔雀石》和一本短诗集,其中大家最喜欢的诗是《鸽子》。 年,张郎郎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美术理论系。 同年因为组织地下文艺沙龙“太阳纵队”,以“恶毒攻击中央首长”、“里通外国”、“阴谋叛国投敌”三条罪名被捕,蒙冤入狱。 年,在北京市看守所学习班用红蓝铅笔和信纸绘制《迷茫》和《往事》,后来同一学习班的范铸明先生将此两幅小画缠成线团带出监狱。 年被判死刑。传说张郎郎因为周恩来总理的一句“留下活口”而幸免于难。 年被改判为有期徒刑15年。 年12月30日被取保候审,回到北京家中。 年至年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员,院刊《中国美术》、《世界美术》编辑。同期画了一批装饰绘画,以及很多以猫为题材的绘画。 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张郎郎改判无罪。 同年在《邮票》杂志发表《从一张邮票谈德加》。 年任《中国美术报》副董事长。 年任《九十年代》杂志专栏作家。 年小说《老涛的故事》荣获《钟山文学奖》最佳中篇小说奖。 同年,朋友孙昌华为张郎郎在美国缅因州立大学举办个人画展。 年作为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学者。 年在香港《九十年代》杂志发表介绍画家刘小东的文章《灼人的阳光》。 年4月16日在最早的中文文学杂志网络版《华夏文摘》上发表文章,这是中国最早的中文网络文学作品,张郎郎也是中国第一个网上文学作家 年由台湾风云时代出版社出版文集《从故乡到天涯》。 同年,朋友孙昌华在美国加州桑塔克鲁茲为张郎郎举办个人画展。 年~年作为康乃尔大学东亚系驻校作家,同时在语言系教授汉语。 年~作为海德堡大学汉学系驻校作家,同时教授汉语及中国文化。 年~年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外交学院教授汉语及中国文化,培养将要到中国工作的外交官。 年由文汇出版社出版张郎郎文集《大雅宝旧事》。 年12月11日~31日在盛世天空美术馆举办“热情.红与黑”个展,展出版画作品15幅。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张郎郎文集《宁静的地平线》。 年7月8日~17日由“秋醒楼”画廊主办、中国地质大学协办、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的张郎郎大型个人画展“一个文人的从心童画”,展出绘画作品60余幅。参加开幕式的有一千余人,前来观看展览的人数超过七千人次。媒体报道:“张郎郎全新感觉的作品给当今绘画艺术带来了一次全新而巨大的视觉冲击”。开幕式当天举行了研讨会,专家、学者、著名艺术家和艺术评论家就张郎郎的绘画进行了学术研讨。著名画家艾轩、著名导演姜文等参观了展览。《人民网》、《新华网》、《雅昌艺术》、《艺术中国》、《凤凰网》等众多媒体对这次展览进行了报道。 年2月在深圳关山月美术馆举办的展览“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家的记忆——大雅宝胡同甲2号文献研究展”展出两幅张郎郎的绘画作品。 4月在上海宝龙美术馆举办的展览“大雅宝胡同甲2号——二十世纪中国美术的传奇”展出一幅张郎郎的绘画作品。 7月由人民东方出版传媒东方出版社出版《郎郎说事儿》。 12月在北京嘉德艺术中心举办的展览“大雅宝胡同甲2号——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历史·现场“展出三幅张郎郎的绘画作品。 扫描偏方治白癜风白癜风规范化
|
当前位置: 饶阳县 >张郎郎意外境地的罗曼蒂克下
时间:2019/3/30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锦绣中国河北威县
- 下一篇文章: 越美越南南宁阳朔桂林越南岘港
- 热点内容
-
- 没有热点文章
- 推荐文章
-
- 没有推荐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