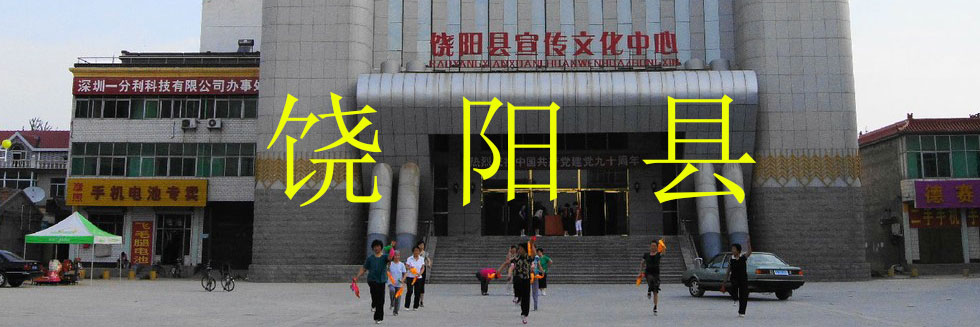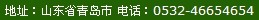|
斗转星移,五百多年过去了,现在这些长城遗迹大多已湮没于荒沙野蔓之中,有些甚至淡出人们的记忆…… 白银境内明长城小考 白银市境内自秦代起就是西北边防要地,并已有长城的修建。据《宋史.地理志》“会州”条记载:“会宁关(故址在今会宁县头寨子乡),北至黄河岸古烽台一百余里”,在宋代而言“古”,时代自应在唐以前,但汉唐时期白银市境属于内地,没有修筑长城的现实诉求也无相关记载,所以只能是秦代的遗存。秦始皇帝三十三年(公元前年),使大将蒙恬北击匈奴,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置44县以守之,白银地区大约于此时纳入秦帝国的版图,并且开始沿黄河修筑防御设施。《宋史》中所说的“古烽台”,当指今靖远县城以东十余里红嘴子坪古烽火台遗址。 宋元时期,干戈纷起,汉、党项、女真、蒙古等民族相继在这里展开激烈的争夺,连绵不断的战火将这一地区闹腾到几于人亡政息。明王朝建立后,只得采取“空其地于河上”的政策,除在迭烈逊(平川区水泉镇黄沙湾)设有一个小小的(从九品)巡检司外,今靖远、平川、景泰三县(区)辽阔的土地上,几乎没有其他行政设置。明前期,国力强盛,朱元璋、朱棣父子挟百战余威,经多次兴兵北伐,终将残元势力驱逐到大漠以北,鞑靼、瓦剌首领都被迫接受了明政府的册封。其时,明王朝的防御重心在河北、山西等近畿地区,西北边防则主要依托汉隋长城旧址,稍加修葺、补筑而已,远在河套以北、贺兰山以西一线。 明宣宗宣德(年—年)年间,鞑靼阿台部为太师脱脱不花所逼,西迁亦集乃路(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一带,游牧之暇,屡次侵扰甘、凉等地,并“间遣轻骑从迭烈逊踏冰入寇,潜窥安(定)、会(宁),以图南寇”。为此,明英宗正统二年(年)始修缮古会州废城(即今靖远县城),置靖虏卫,领千户所四,辖境囊括了今白银市三县两区大部之地,设重兵拱卫。在蒙古铁骑的强大压力下,白银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天顺、成化之际,鞑靼阿罗出、孛来、小王子、毛里孩等部相继进据河套地区(明史称为套虏),频年南下寇掠,渐成明王朝西北边防的腹心之疾。为了遏制鞑靼的侵略,成化十年(年),宁夏巡抚徐廷璋主持修筑边墙(明人称长城为边墙)一道,东起花马池接延绥镇长城,西抵灵武横城堡黄河岸边,全长三百八十七里,是为“河东墙”,又称“横城大边”。成化十三年(年),贾俊继任宁夏巡抚,在职七年,将“河东墙”向北向南大加拓展,其间“修宁夏西路永安墩至西沙嘴一带边墙”。(顾祖禹《读书方舆纪要》)永安墩即今靖远县双龙乡永安堡,西沙嘴在宁夏中卫市西园乡黑林,长城由此沿黄河南岸西行,经南长滩、香山,在芦沟进入靖远地界,然后经北滩、永新、兴隆等乡,止于永安,此为明王朝第一次在白银境内修筑长城。这一段长城一百多年后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公元年,即明神宗万历二十四年,明政府尚在其中段修筑了规模宏伟的芦沟堡,遗址迄今犹存,其它如墩台等遗迹更是相望于道途。 然而仅一条“横城大边”怎能挡得住鞑靼人的无休止地入侵。明孝宗弘治十四年(年),“小王子以十万骑从花马池入,散掠固原、宁夏境,三辅震动,戕杀惨酷”。(《明史·鞑靼传》)此次事件在明廷上下引起极大震动,翌年,明朝廷特地在宁夏镇以南划出一个军事防区来,成立固原镇,三边总制秦紘又奏准于其北境修筑边墙一道,史称“固原内边”。这一道边墙以徐斌水(今宁夏同心县东北徐冰水村)为界,分东西两段,东段起自徐斌水,东抵饶阳水堡(今陕西定边县姬原乡辽阳村),凡三百里;西段起自徐斌水,止于靖虏卫花儿岔,凡六百五十里。花儿岔在今平川区水泉镇水泉村,鞑靼自迭烈逊或老龙湾踏冰来犯,这里是必经之地。岔口的山梁上,长城遗址岿然犹在,望之仍觉气象森严。明边墙由此发端,一路向东略偏南行,经东升、靖安、宝积、靖安、共和、黄桥等乡(镇),穿过黄家洼山,进入宁夏海原县乾盐池(时属靖虏卫管辖),然后折向东北,达于徐冰水。由于这一地带土质疏松,黏度小,而且高山深谷居多,修建时只能“开堑斩崖筑墙,各因所宜”,(明魏焕《皇明九边考》卷一),以此这一带长城便具备多种形态,既有夯筑的土墙,也有垒砌的石头墙,但更多的是铲削山崖而成的石壁和人工开掘的壕堑。嘉靖九年(年),三边总制王琼又进行大规模的整修,从此更加“深险壮固”,“屹然为关中重险”。(《皇明九边考》)今天,在平川区黄家洼山一带,仍可以大致领略当年的风姿。这里是著名的青砂岘所在,长城遗址穿行于山脊,轮廓清晰可见,墙体残高约1-4米,壕堑宽约6米,在制高点上建有烽火台,台高约6米,主体用黄土夯筑,外围用青石板铺砌。环烽火台筑有圆形的堡墙,残高约1米左右,其西南有堡门的遗迹。堡、台、墙、堑构成严密的防御体系,明代戍边将士之用心良苦,可见一斑。明世宗嘉靖(年—年)初年,鞑靼宾兔、阿赤兔、宰僧等部盘踞大、小松山(明史称为“松酋”,山在今景泰、古浪、天祝三县交界,或曰即今景泰县寿鹿山、昌林山),其势力不断向南扩张,如一把利刃楔入兰(州)、靖(虏卫)、庄(浪,今永登)、凉(州)腹地,黄河以北大片沃土沦为樵牧之地。鞑靼人肆无忌惮地在黄河对岸饮马、放牧,甚至扬言要夺取兰州镇远浮桥,河防骤然吃紧。冬季情势尤其严峻,《皇明九边考》有云:“靖虏一带每岁黄河冰合,一望千里,皆如平地”,鞑骑“乘间窃发”,真是防不胜防。早在弘治末年,卓有远见的杨一清为陕西巡抚,曾经“筑垣濒河以捍靖虏”。(《明史本传》)嘉靖九年,王琼“又自花儿岔起西至兰州枣儿沟止,开堑三十四里”。(见《皇明九边考》,数据恐有误,明张雨《边政考》云:“起甜水堡,至兰州,因地形势,挑壕堑八百里,据险以守,边人至今便之。”)嘉靖二十七年(年)王以旂总制三边,在此基础上增筑墙垣,遂形成兰州至靖虏卫之间的河防体系,史称“黄河一条边”。根据《读史方舆纪要》所附九边地图推断,此边墙自大浪沟进入靖虏卫地界,顺黄河而下,经苇子湾、平滩堡、营防滩、虎豹口、红嘴子至靖虏卫城,然后东行过癿肚子、大坝渠、红柳泉,陡城堡、迭烈逊,沿水泉沙河至花儿岔,与“固原内边”连为一体。其中“平滩堡东西沿河五十里,俱无边墙,惟斩土石,作坡坂而已”,自靖虏卫城而东,则边墙与壕堑相参,据记载,上世纪五十年代,三合(癿肚子)、大坝等地明边墙遗址犹存,后毁于平田整地中。 是时,明军退据“固原内边”之南,“内边”以北裴家川、乱古堆一带,从此被弃置徼外。明人所谓裴家川,范围很广,包含今靖远县石门、双龙、永新、兴隆、北滩等5个乡镇的大部及宁夏中卫市南、北长滩等地,“其间有腴田万顷,军民岁以寇患,不得田作”。为了恢复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明穆宗隆庆三年(年),靖虏卫贡生高冠上书兵部尚书霍思齐,“议设沿河堡屯要隘,以省虚糜,以消虏患”,引起明朝廷的高度重视。隆庆五年(年)六月,在三边总督王之诰的主持下,开始于裴家川黄河东岸修筑长城,其北起自靖远与中卫交界的喜鹊沟,南至平川区水泉镇玉碗泉村,中经大庙墩、马尾沟、大碾子、急山湾墩,小红沟口、消水墩、迭烈逊口墩等“隘口”,全长里,其中土筑边墙50里,无墙斩坡边余里,前后历时五月,全线告成,史称“裴家川长城”。万历二十六年(年),明王朝发动大、小松山之役,一举奏捷,“攘地五百里”,将盘踞于此达半个多世纪的鞑靼各部驱逐到贺兰山西。战事甫毕,三边总制李汶亲赴松山以北实地踏勘,决计修筑一条横贯东西的边墙,以防止鞑靼卷土重来。这是明王朝最后一次大规模地兴筑长城,据荆州俊《三眼井堡记》载,此工程“起工于万历二十七年三月,至六月事竣,凡筑边自乌兰哈思吉至大靖泗水堡,延袤四百里”,是谓“松山新边”,或曰“万历新边”。乌兰哈思吉,即今靖远县石门乡黄河东岸的哈思吉堡,“新边”由此发轫,经索桥过黄河,进入今景泰县境,然后西北行经东关村、西关村、麦窝至芦阳镇,再经城北墩村、西一泵,跨京兰跌路,过八道泉村、青石洞村,越夹山泉山至红墩子村,又过高家墩、保进墩,由毛牛圈村西北出景泰县界而入古浪,止于武威市黄羊镇泗水堡村,其中景泰境内全长约里。 要之,明王朝在今白银市境内修筑长城规模较大者先后有五次,分别属于“横城大边”、“固原内边”、“黄河一条边”、“裴家川长城”、“松山新边”,其中“裴家川长城”全线在白银境内。由于特殊的地理地貌环境,这些长城多因地制宜,呈现为墙、堑、沟、壕、坡、坂、墩、台等丰富的样态,这一方面体现出明朝先民们的智慧,另一方面也似乎表明,虽然经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他们也并没有便把此边墙视作一劳永逸的分界线,而略带有临时防御的性质,一待时机成熟,他们依然不忘及时收复故土,譬如大、小松山之役即是如此。 斗转星移,五百多年过去了,现在这些长城遗迹大多已湮没于荒沙野蔓之中,有些甚至淡出人们的记忆。但是,当你行走在白银大地上,时不时仍会看到那些经历数百年风风雨雨,依然挺立在高山之巅的烽燧遗址,仿佛在召唤你拂去历史的尘埃,探寻祖先的足迹……(图片由地方文史研究者单顺朝先生提供,在此谨致谢悃!) 作者简历高云鸿,男,年出生,甘肃靖远人。年毕业于兰州医学院药学系,现医院,承乏办公室主任之职。白银市史地学会会员。少嗜文史,尤留心于地方文献掌故,学生时代曾在《甘肃日报》《兰州晚报》等报刊发表相关文章20余篇。-年应靖远县人民政府之聘,参编《靖远县志》。 陇上风情支持原创,点击赞赏
|
当前位置: 饶阳县 >白银境内明长城小考高云鸿
时间:2021/6/21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建国后河北省沧通定三个专区演变
- 下一篇文章: Ap71衡水志臻中学安平校区清河校区
- 热点内容
-
- 没有热点文章
- 推荐文章
-
- 没有推荐文章